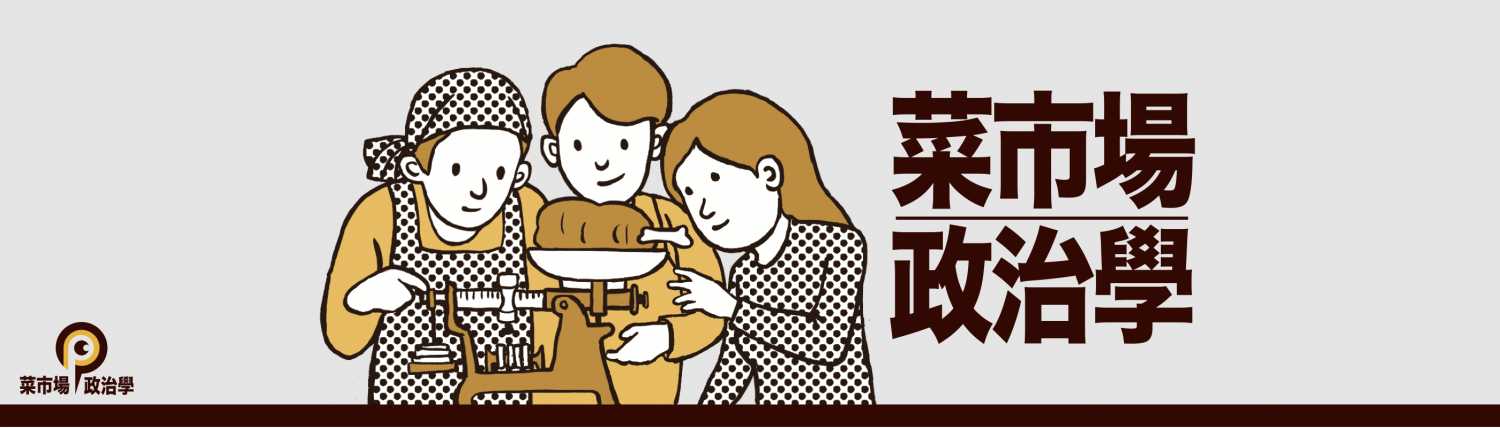◎吳乃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 本文原刊登於中國時報,2006/2/27。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如此描繪記憶女神:女神有兩個面孔,一個面孔凝視過去,另一個面孔則正對現在;一手抱一本書,另一手則拿著鵝毛筆,準備書寫下一章。這正是集體記憶最佳的寫照:記憶以過去為材料,可是書寫的目標卻是為了現在,以及未來。
歷史記憶經常為了迎合現在的需要,對過去做剪裁和闡釋。然而現在卻經常是分裂的。用歷史記憶來啟發現在、指引未來,必然面對質疑:誰的現在,你的還是我的?甚麼樣的未來,統一還是獨立?歷史記憶因此也經常是衝突的,而且也永遠隨著時代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內涵和啟示。
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中最巨大的創傷。雖然我們將這一天訂為「和平日」,我們對它的回憶卻充滿了火藥的煙硝。歷史回憶的對立來自兩個重疊的根源。一是「現在」政治利益的衝突;另一則是對「未來」的不同願景。前者是政治的恆常,後者短期間內不可能消失。可是難道在現階段我們不能擁有一個共同的二二八?無法讓它成為我們這個政治社區共有的、可珍惜的歷史回憶?

圖片:近來有許多由民間發起的二二八紀念活動,共生音樂節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2017年的音樂節「228共生音樂節─欲行 ê 路」也正在進行群眾募資。圖片截自flyingV群眾募資提案專頁。
記憶不完全等同歷史
目前對二二八事件的爭論之一,是歷史記憶和歷史事實之間的差距。全世界所有的民族的集體記憶中,巨大創傷都是的重要元素。「在民族的記憶中,苦難通常比勝利更有價值,因為苦難要求責任、號召集體的奉獻。」因此所有的民族都強調、甚至誇張其苦難。戴高樂宣稱法國是全宇宙最苦的民族,因為她曾經四次被佔領。常被瓜分併吞的波蘭人顯然不會同意這個論斷。遭受屠殺浩劫的猶太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巴勒斯坦人更會大聲抗議。
歷史記憶是創傷的轉化。它並不完全等同於歷史,雖然也不能違反歷史、竄改事實。在集體記憶中,歷史只是骨架,更重要的是血和肉:歷史的反省、教訓、和啟示。「集體記憶將歷史的單一事件轉化成原則性的訓示,這個訓示可能是正義原則、或政治理想、或道德規則。」台灣認同者對二二八事件轉化的歷史記憶是:外來政權的災難、菁英同胞的抗暴和悲慘的犧牲。
歷史記憶、或歷史啟示要產生效力,必須和當代社會的主要關心有所共鳴。台灣認同者對二二八的解釋之所以被廣泛接受,正因為它在台灣政治發展的兩個階段中,都和台灣人對自主性的期待產生共鳴。在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下,這段歷史雖然是禁忌,對它的記憶仍然在民間被鮮活地保存了四十年。這段記憶在暗中的保存、加工、和傳遞,是當時人民對抗專制統治的唯一工具。正如昆德拉在《笑忘書》中所說的,「人民對權者的抗爭,就是記憶對遺忘的抗爭。」
在現今的民主階段中,由於中國政權對台灣人民自主性的否認和威脅,二二八集體記憶的主題「外來政權的壓迫、反抗、和創傷」,持續和人民產生共鳴。只要台灣的自主性持續受威脅,這樣的闡釋將繼續在社會中產生共鳴。
正如中國認同者所質疑的,這樣的闡釋其實違反歷史事實。事實上,台灣認同者對二二八的論述,也經常將「歷史闡釋」和「歷史事實」混淆。中國認同者認為該事件並不是民族壓迫,甚至不是省籍矛盾、族群衝突,不是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對抗,而是人民對腐敗政府的抗議。這樣的論斷應該比較符合歷史事實。從這個事實出發,二二八的歷史教訓比較是政治權力的恐怖,以及獨裁政治對人道的殘害。
闡釋和事實的對立,來自認同的差異。兩者之間有對話的空間嗎?或許困難,可是並非不可能。雙方都必須理解,歷史記憶和歷史事實並不等同。一方面,教訓和啟示不應被當成事實來闡揚。如果我們對逝者仍有責任,責任之一就是將真相和事實還給他們。而且,當我們將啟示和事實混淆,我們等於是告訴另一個族群的同胞:我們自始就沒有將你們當成自己人,我們的犧牲也是來自你們的不義。這不但違反歷史事實,也妨害我們建立共同的政治社區。
我們也應理解,民眾之所以能和偏離事實的歷史記憶共鳴,正是因為目前的處境,而不一定是因為族群的排斥。不論我們對未來的想像是獨立還是統一,我們共同的自主性被中國政權否認和剝奪卻是一個事實。我們也因此在國際社會中,處於「社會性死亡」(social death)的狀態:生物層次上我們仍然活著,可是我們的身份、人格、和存在完全不被承認。這是我們的共同處境。讓「自主」成為二二八歷史記憶的基調,或許也符合我們的共同利益。

圖片取自民報。原出處:新生報,1947.03.11
政治利益的糾葛
除了認同的差異,政治利益、或黨派利益也造成二二八歷史記憶的對立。在民族的重大創傷中,一定有壓迫者和犧牲者,有好人和壞人。犧牲者值得懷念,壓迫者必須譴責。可是這個創傷距離我們仍然不遠,在好人和壞人的分辨中,有些政黨得利、有些政黨蒙羞。
此種歷史記憶和政黨利益的糾葛,發生在許多新民主國家中。二次大戰前的內戰是西班牙的歷史創傷。在民間的歷史記憶中,勝利的法朗哥政權是壓迫者和屠殺者。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為了轉型順利和社會和諧,雙方約定對這段歷史做「刻意的遺忘」。可是一九九六年西班牙國會卻打破這項約定,通過法案賦予「國際縱隊」的成員西班牙公民的身份。國際縱隊的四萬多成員來自世界各國(其中一萬六千人陣亡),光是美國就有三千多人參與,幫助西班牙人反抗法西斯政權。參與者中許多為知識份子,如英國的歐威爾。海明威亦以戰地記者的身份、以及他的經典名著參與了內戰。重提這項歷史記憶,自然不利於和法朗哥政權有歷史淵源的民眾黨。該黨的政治領袖因此拒絕參與所有的典禮和儀式。
二二八的歷史記憶,對國民黨確實不利。可是我們難道不能跨越黨派之私,讓這段歷史成為全民可以共享的記憶?雖然困難,可是並非不可能。首先,我們有絕對的道德正當性譴責加害者。可是道德上正當的行為,政治上不一定合宜。在口語上聲討「元兇」及共同加害者,有其道德的正當性。可是,揭發歷史真相本身就是最佳的譴責。將歷史記憶兌現為短期的黨派利益,不但貶低了民族創傷的神聖性,也無助於共同政治社區的形成。沒有真相就不可能有和解,可是真相本身並不能帶來和解。
台灣是一個分裂的社會。彌補裂痕、團結成單一的政治社區,不是靠制度或政策,而是公共人物的言行和智慧。《還原二二八》這本書的扉頁上這樣說:「受夠了政治口號的二二八,受夠了那些吵個沒完沒了的補償金,受夠了哭哭啼啼,講不完台灣人的悲哀。」不能以同理心來看待同胞的傷痛,和將同胞的傷痛兌現為政黨利益,效果一致:不但無助於團結,反而加深分裂。
對過去,我們有不同的經驗;對未來,我們有不同的願景;現在我們對政黨有不同的喜好。可是不論我們喜不喜歡,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政治社區中,我們都是政治伙伴。維持這種伙伴關係並不容易,民主也不容易。
二二八應該是我們可以共享的歷史記憶。它包含了壓迫和反抗、殘暴和仁慈、投機和理想、出賣和忠貞、麻木和溫情、男人的血和女人的淚,是我們這個社區唯一可以共有的史詩。為什麼不珍惜它,用我們的謹慎、慷慨、和想像力,讓它成為團結我們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