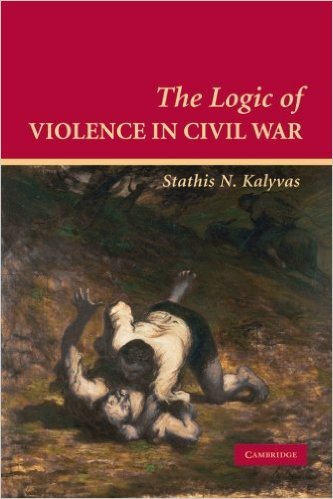◎ 蘇慶軒/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作者曾在〈菜市場政治學〉的前兩篇文章中提到國家權力與國家形成的概念,本文試圖延伸這兩個概念,討論統治者是如何使用國家暴力維持他的統治地位,並以包括台灣在內的威權統治經驗進行舉例說明。
就概念上來看,威權統治者通常將政治異議界定為「敵人」、「罪犯」與「病患」等三種身分,「敵人」是構成「罪犯」與「病患」的基本要素,「罪犯」則是組成「病患」的元素之一(如圖1)。
敵人:一個內戰的觀點
反抗統治的極端形式是作為國家的「敵人」,並發動「內戰」挑戰統治者。反之,統治者若想支配社會,則需先消滅反抗統治的敵人。因此,社會學者傅柯認為,戰爭並不只發生在國境之間,也發生在國境之內,並展現在權力關係中支配與反抗支配的衝突上(鄭祖邦,2014:80)。傅柯指出,為了維護支配關係與社會秩序,「政治」便成為防止國內動亂的基本手段,因此「政治是戰爭以其他手段的延續」(汪宏倫,2014:12-13;鄭祖邦,2014:69-80)。
借用傅柯的觀點,如果將反抗威權統治的政治異議(視為「叛軍」)與統治者(視為「政府軍」)之間的關係,視為兩軍交戰,那麼可以想見,叛軍的理想是發動革命推翻統治者。在叛軍實力足以發動革命之前,只能想盡辦法藏匿在政府軍控制的領地,透過散播革命的理念爭取其他人的認同,以此儲備革命的能量,並靜待革命的時機。
另一方面,對政府軍而言,如何搜捕叛軍是一個統治上的難題,因為叛軍會試圖偽裝成公民,藉此增加政府軍辨識上的難度,躲過政府軍的搜捕。政府軍因此被迫要面對一個問題:該如何辨識叛軍?政府軍的難題可以借用表1說明。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決策的後果可能是成功地「綏靖」叛軍1,但也可能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予以「縱放」。政府軍倘若判斷錯誤,有可能傷及無辜而形成「冤錯假案」,如何形成「精準的判決」,成為政府軍必須面對的問題。
政治學者Kalyvas從政府軍的困境中2,指出兩種內戰中常出現的國家暴力形式為選擇性的暴力(selective violence)與無差別的暴力(indiscriminate violence),(2006: 142)。選擇性的暴力多以「行為」界定政府軍所要施暴的對象,在內戰中最常用的依據是「順服/合作與否」(Kalyvas, 2006: 26,173)。無差別的暴力多以「類別」界定政府軍所要施暴的對象,在內戰中最常用的類別是「地點」(Kalyvas, 2006:148)。也就是說,導致國家暴力差異的原因,在於政府軍有無足夠的資訊辨別叛軍,若無法辨認叛軍,則有可能在特定的地點使用無差別的暴力。
圖片來源:Amazon
Kalyvas指出,不論政府軍使用哪一種暴力,其目的皆是為了散播「恐懼」(fear),恐嚇平民不得背叛,強制平民與政府軍合作(2006:23-26)。若對暴力作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發現施暴是為了改變叛軍、政府軍與人民之間的均衡狀態,回溯特定人物過去的(不合作)行為進行相應的施暴,已達成前瞻性的效果,使他人因恐懼而不敢重複該特定人物過去的(不合作)行為(Kalyvas, 2006:27)。
除了恐懼(棍子)之外,還有其他誘因(胡蘿蔔),如內戰中因資源不足導致經濟上或安全上的需求,使被統治者需要受到保護或者獲取資源分配(如食物配給)(Kalyvas, 2006:114-115)。若被統治者願意與政府軍合作,長期的合作關係會使被統治者會產生「忠誠」(loyalty)而疏離叛軍,至此,政府軍才算真正「擁有」這塊領土與平民(Kalyvas, 2006: 128)。
1947年228事件是戰後台灣最接近內戰狀態的衝突,事件中國民黨軍曾使用「無差別的暴力」,如3月8日21師登陸基隆港時,曾對港岸進行無差別掃射,登陸後又在港邊濫捕濫殺,過程中不論槍口下的這些人是否曾經抵抗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國民黨軍亦有使用選擇性的暴力,系統性地迫害特定人士,如殺害台南律師湯德章、畫家陳澄波等曾經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台籍菁英。事件後國民黨軍又實施戒嚴,進行「清鄉」,迫使事件中以反抗國民黨政府的謝雪紅、楊克煌等人逃到香港。國民黨政府回溯台籍菁英在事件中提出各項具有自治精神的訴求,針對性地懲罰他們試圖出面平息事端的行為。與此同時,施暴的效果也具有前瞻性,透過暴力的展演,讓台灣社會不敢公然重複事件中抵抗統治的行為。
1947年3月8日國民黨軍在基隆港無差別式的屠殺。圖片來源:民報
國民黨政府以武力為後盾,重新控制台灣,只不過1948年國共內戰情勢逆轉,共軍來勢洶洶,國民黨政府的存續已然成為一個疑問。
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政府的撤退路線。圖片來源:Wikipedia
罪犯:一個以法統治(rule by law)的觀點
1949年國共內戰的情勢明朗,似乎要以國民黨敗亡而結束,因此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及其下個支部、委員會等組織因此不斷擴張。但1950年6月韓戰爆發,台共與中共可以裡應外合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可能性消逝,國民黨政府在美國的庇護下存活下來。為了鞏固統治,國民黨政府必須再次「綏靖」台灣,緝捕台共組織成員。於是,國民黨政府同樣要面臨前述政府軍的困境,如表2。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只不過,這次的困境與內戰不同,「綏靖」不能直接訴諸暴力,而是必須「於法有據」,依據戒嚴體制與相關法令將鎮壓合法化,以法律「制裁」反抗統治的行為,使「敵人」成為威權政體下的「罪犯」。
Davenport將「國家鎮壓」分成兩種類型:對「公民自由的限制」以及「人身(格)侵犯」3(2007a: 2;2007b: 487)。國民黨政府在1950年代初期鎮壓共黨組織成員的手段,多採用「人身(格)侵犯」,以殺害與監禁的方式進行,使馬場町成為著名的刑場,綠島成為監禁政治犯的監獄之一。國民黨政府在整肅台灣社會內部的左翼勢力後,鎮壓方式逐漸減少「人身(格)的侵犯」,而越趨使用「公民自由的限制」,使國家鎮壓強度從1950年代之後就開始下降,威權統治越趨穩定4。此一趨勢與比較政治的研究成果相符。
Davenport比較一黨專政、個人獨裁與軍事政體後指出,雖然傳統上認為馬列政體(Marxist-Leninist Regimes)鎮壓最烈,但一黨專政政體(馬列政體通常都是一黨專政)在「人身(格)侵犯」與「公民自由的限制」上的鎮壓程度是最低的(2007b:500)。因此一黨專政政體可能是在建立之初採行高強度的鎮壓,使日後可以減少強制力的使用,而偏向以限制公民權利的方式進行統治(Davenport, 2007b: 500)。此外,Davenport認為政體有無能力進行「引導管制」,影響了該政體的鎮壓強度,因此馬列政體鎮壓程度之所以最低,可能與該政體具有全面掌握社會的統治能力有關(2007b: 486)。
其他威權政體中「罪犯」的例子:1989年中國民眾蕭斌接受外媒訪問,他批評中共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的暴行。中共在攔截外媒的衛星訊號後得知此段訪問,通令全國發布通緝,在其他民眾的舉發下,蕭斌被捕,遭求刑十年。圖片及資料來源:YouTube
相關新聞與補充說明: 2011年9月29日《中國時報》刊載一篇關於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報導〈中將吳石匪諜身分曝光 破獲最大共諜案〉,居然輕信國防部保密局處長葉翔之的自述,離譜地寫下與歷史事實完全不相符的說法:「在葉翔之請命下,一場震動全台,本來不該留一個活口的共諜案,最後卻是喜劇收場,沒有一人遭槍決」。10月5日一位匿名的「倖存的台共」投書蘋果日報民意論壇,痛斥這樣的說法,且自白自己雖投身革命,但被捕後卻因為軟弱交出同志的名單,此後過著內疚而備受精神折磨的日子: 「回到家鄉經過輾轉打聽,我才知道同一小組的同志全部遭到槍斃,我內疚到想要自殺,數度徘徊於鐵路旁邊,但是因為懦弱與苟且偷生,始得活至今日來寫這篇文章。我想對葉祥之、谷正文之流的特務表示,當年為了革命,雙方已經進入作戰狀態。我們同志被殺無數(目前知道的數字在千人以上),但我可以了解你們為了保衛政權的殘酷手段,換做是我們革命成功,我也可能做出同樣殘酷的事情。只是,一場雙方交鋒的血戰,你們竟然用『喜劇』、『沒有一人遭到槍決』的荒謬說法來矇騙大眾,敢做不敢當,實在與你們在保密局的囂張模樣相差甚遠。我是一個早該死去的年邁之人,希望我的痛苦回憶,能夠為這段時代的悲劇留下一點可靠的痕跡。」 (刊載於蘋果日報民意論壇,2011/10/5,「葉翔之睜眼說瞎話」。)
換言之,國民黨政府來台初期為了建立國家統治機制、清剿共黨組織成員,而實行高強度的鎮壓。但1950年代以後之所以能夠減少「人身(格)侵犯」而日趨使用「公民自由的限制」,在於國民黨政府的統治能力已使戒嚴法等法律體制並非徒具形式,而是有能力執法,對社會進行「以法統治」(rule by law)。國民黨政府龐大的黨政官僚體系支撐了「以法統治」的支配方式,使統治者足以進行諸如政治參與的限制、集會結社自由的限制、言論自由的限制、出入境的限制、對外經貿的限制、藝文娛樂上的限制、出版的限制…等等。違反法令限制者,即使無意挑戰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也會受到相應的法律懲處,因此「罪犯」所涵蓋的對象是廣於「敵人」(如圖2)。此外,原有的「敵人」也從共產黨人往外擴張,擴及追求民主自由的黨外人士以及主張台獨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即使這三股勢力歧異甚大,各勢力內部也有分歧,但國民黨政府仍將之視為「三合一敵人」。
不過「以法統治」有其極限,統治者即使透過官僚體制管制人民的身體,限制人民的行為,但還是可能有人持續抵抗統治。於是,比「以法統治」更為細緻的鎮壓方式,是將這些具有抵抗意志、無懼於罪刑加身的個人,視為需要治療的「病患」,摧毀他們據理力爭時展現在臉上的自信。
請搜尋「余澎杉(Amos Yee)」,這位少年的處境需要您的關心。圖片來源:Channel NewsAsia
統治者如何將政治異議者視為「病患」,而此種鎮壓方式又會產生何種效果,我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做說明。
參考書目
- 鄭祖邦,2014,〈戰爭與社會理論:一種現代性的視角〉,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市:聯經,頁35-96。
- 汪宏倫,2014,〈把戰爭帶回來-重省戰爭、政治與現代社會的關聯〉,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市:聯經,頁1-34。
- Kalyvas, Stathis. 2006. 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enport, Christian. 2007a. “State Repression and Political Order.”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0: 1-23.
- Davenport, Christian. 2007b. “State Repression and the Tyrannical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4: 485-504.
相關文獻與連結
- 若對鎮壓如何產生作用感到興趣,請參考:Siegel, David. 2011. “When Does Repression Work?: Collective Ac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Journal of Politics 73(4): 993-1010.
- 錢鋼在《風傳媒》提出一個對1989年中共的觀察:〈錢鋼語象報告:「敵對勢力」在一九八九〉,可以作為威脅威權統治而被視為「敵人」的一個案例。錢鋼用「敵對勢力」在《人民日報》的出現頻率推測中共對內進行整肅的強度: http://www.storm.mg/article/23465
- 「綏靖」可以理解成「平亂」,任何足以壓制反抗的方法皆可視為綏靖的手段,諸如安撫、攏絡、收編、武力鎮壓、甚至挑撥離間,分化反抗陣營等,皆是綏靖的手段。 ↩
- 在Kalyvas的研究中,政府軍與叛軍是兩個對等的行為者,因此Kalyvas對於政府軍施暴的原因與方式,亦可套用於叛軍那一方。本文是為了行文方便而以政府軍作為論述的主角,而非刻意製造「政府軍才會施暴」的印象。此外,這裡補充文中兩種暴力的歧異之處,以受害者的角度來看,選擇性暴力的施暴對象通常是個人為單位(personalized targeting),無差別暴力的施暴對象則是以集體為單位(collective targeting)(Kalyvas,2006:142)。 ↩
- 「公民自由的限制」(civil liberties restrictions),是指以諸如法令限制等方式「管制引導」反抗的時機與地點(channeling opportunities);「人身(格)侵犯」(personal integrity violations),則是指國家試圖透過諸如監禁、殺害等方式排除目標人物(eliminating actors)(Davenport,2007b: 487)。 ↩
- 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提供戒嚴時期部分已知的槍決名單可供參考,槍決人數以1950年代為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