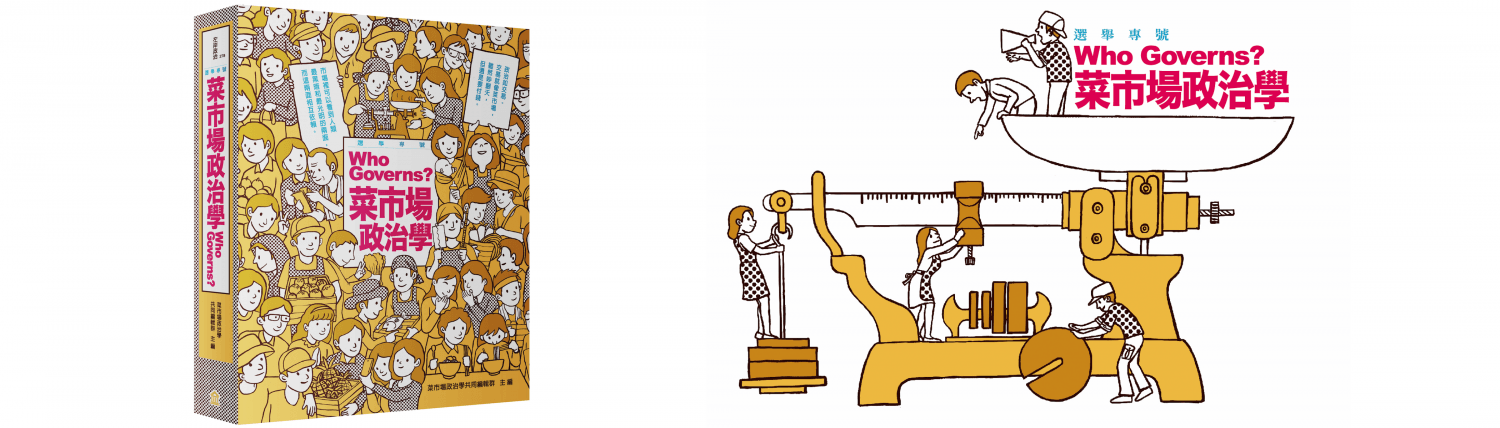◎吳乃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 本文原刊登於《思與言》47, 3 (2009, 9): 1-25,以及作者部落格,連結請按此。由作者授權菜市場政治學刊登。
對加害者做法律的起訴或道德的控訴,是轉型正義的主要任務之一。這項任務的前置工作是對加害者及加害行為做完整和深入的理解。每一個國家的威權歷史和威權情境都不盡相同,對加害者的態度因此也必然有所差異。不論台灣是否對加害者做法律或道德的追訴,對邪惡行為的反省都是必要的工作。
這項反省是建立民主文化的基礎工作之一。雖然民主化已超過二十年,可是台灣在這方面的工作卻尚未開始。本文討論鄂蘭「邪惡庸常化」的概念:納粹領導人乃是一般的正常人,其邪惡行為主要來自對政治權威的無條件服從。鄂蘭的理論在過去三十多年產生巨大的影響,是政治哲學討論邪惡的起點。本文指出,鄂蘭對納粹領導人的理解是錯誤的,她對邪惡的解釋也非常片面。艾緒曼事實上是一個強烈的反猶太主義者。然而,鄂蘭卻指出了一個政治哲學中恆久的議題,以及所有政治體制中的公民所面對的普遍課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不義的權威?
哈伯瑪斯:波蘭是如何處理過去的?
米克尼科:在波蘭每一個人用他自己的方式處理。當我們贏得1989年的選舉,我馬上和那些將我關進監獄裡面的人正常地談話聊天。我想,這是啟蒙的辯證功能。…長久以來我一直相信,政治陣營不應該以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來分類,而應該以未來會發生的加以分類。
哈伯瑪斯:我知道你目前和傑魯斯基將軍維持甚友善的關係。我忍不住將你的態度和那些70和80年代離開東德的作家們相比。
米克尼科:因為他們移民國外,而我留下來了。…我認為沒有任何東西像仇恨、及報復可以那樣地摧毀一個人。…在監獄中,我閱讀三位德國作家:托瑪斯曼、哈伯瑪斯、和潘霍華…所以我就想出了「我們應該赦免加害者、但是同時也不遺忘歷史」這個公式。1
米克尼科(Adam Michnik)是當今波蘭社會的良心。他不追究加害者的主張,在波蘭引起甚大的爭論和批評。對於威權政體中號令、執行、或支持人權侵犯的人,我們應該如何加以對待,始終是一個複雜的政治和道德難題。即使我們贊同米克尼科的主張和道德胸襟,曾經歷過大規模政治迫害的社會,仍然不得不回答:眾多積極支持政治迫害體制的人,應付何種道德責任?近幾年轉型正義在台灣受到很大的關注。可是我們至今很少提出這個問題,遑論有系統地回答它。而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又不得不先回答:他們為何執行、或支持侵害人權的行為?米克尼科的「不應遺忘的歷史」,應該也包括:眾多的人曾經基於某種原因而積極或消極地支持迫害體制。新民主社會對威權統治的反省,必須包括這個歷史現象。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對加害者動機所提供的解釋,則是討論這個重大問題的起點。然而,鄂蘭的解釋─對權威的盲目服從忽略了重要的歷史事實,不但過於單純,也非常片面。
轉型正義不只是一項政治措施,一項新民主政府針對獨裁政權的人權侵犯行為,所從事的賠償和追訴、或追究的工作;轉型正義同時也是一個文化反省運動,一個從歷史反省中建立民主文化的運動。可是建立民主文化有那麼重要嗎?我們不是已經處在民主時代,民主不是已經成為世界的主流?認為專制獨裁已經一去不復返、而民主將永存的人,在仔細觀察媒體、特別是電視上的政治性談話節目之後,或許不會如此樂觀。對自己領袖或政黨的無條件支持、甚至效忠,將對方視為敵人或病菌,這樣的心態在過去曾經為許多獨裁政權的出現提供了文化基礎,也是大規模暴行得以順利維持和運作的有利條件。我們今天所觀察到的令人擔心的政治文化,和過去在程度上或有所不同,本質或許沒有太大的差異。獨裁和政治壓迫可能由各種不同的因素所催生,宗教的、階級的、民族的、或族群的。如果我們曾經較細緻地處理過轉型正義的文化反省面,我們或許比較能避免不自覺地落入這樣的危險心境。
足以顯示轉型正義的文化建設面受到忽視的例子,是一個表面看來似乎無足輕重的小事。2007年三月,國民黨公布了民進黨幾位高階層領導人過去加入該黨的記錄。(中國時報2007/3/02) 同年十一月,該黨又公布了兩位以攻擊國民黨為職志的電視主持人的入黨記錄。(中國時報2007/11/14) 相同的事情發生兩次,應該不是組織決策系統的失誤,而是該黨深思熟慮的行為。這個行為反映出,建立威權獨裁體制的國民黨對它過去的所作所為,似乎仍然不覺得有錯。在當時強大的黨國體制下,許多年輕人或因為政治知識的缺乏,或貪圖工作的方便,或缺乏足夠的勇氣拒絕來自體制的遊說和引誘,而加入迫害人權的政黨。對後來有幸覺醒的人而言,不論當初是基於是無知或貪圖方便,總是一個難以消除的羞愧。如今國民黨卻將這個加害行為當做嘲笑對手的材料;正如刑求者展示捏造的自白書、性侵害者展示受害人的照片來羞辱受害者。國民黨這種行為充分顯示,我們的社會仍然缺乏最基本的是與非、善與惡的觀念。部分原因或許是,我們社會對過去的錯誤從沒有進行過普遍性的反省。
國民黨立委楊鎮浯於2016年12月21日質詢黨產會主委顧立雄,指出他曾加入國民黨,想要諷刺說他很「聰明」,因為當時大家都流傳一句話:「你要去當兵,最好是國民黨籍的比較好。」影片來源:請按此。
而民進黨政府高層對這件事的反應,也顯示轉型正義工程中文化價值面向的受忽視。民進黨高層許多人對年輕時代加入國民黨的回應,有些人說是為了工作,有些是為了升遷,有些則說是為了出國。以他們後來對台灣民主所做的貢獻,他們其實可以對這個行為說得更多,讓它成為全社會反省的教材。可惜因為他們的惜言,社會失去一個絕佳的反省機會。
我們之所以未能在追求轉型正義中,藉助對過去的反省來建立民主文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或許是轉型正義在台灣的遲延。一般而言,追求轉型正義最可能的時機是緊隨威權獨裁政府崩潰之後。在那樣的階段中,舊有的統治團體和加害者不再掌握權力,而人民對政治迫害的記憶猶新、憤怒尚未消除,對正義的渴求也較為殷切。可是,台灣的民主轉型卻非來自威權統治團體崩潰和喪失權力。相反的,台灣的民主轉型是由威權統治團體對民主要求做出退讓而完成;同時,在民主化之後威權統治團體又繼續統治了12年。威權的統治團體自不可能真誠地面對自己的過去。直到現在,國民黨已經失去政權的八年之後,其領導階層都仍然是當初威權體制的核心成員。因此,在國民黨統治期間,台灣處理轉型正義唯一的工作是「補償」受害者。對轉型正義的其他兩項重要工作,追訴、或追究加害者以及追求歷史真相,幾乎完全忽略。2
民進黨執政之後,一方面「壓迫時刻」的久遠(台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政治壓迫案件發生於1970之前),造成人民的冷漠;3 而另一方面執政的民進黨也沒有將轉型正義列為執政的重要工作。文化價值似乎不是民進黨所關心的議題。歷史真相的發掘進度遲緩,民主文化的建設工作也因此無以展開。至目前為止,政治迫害檔案的蒐集和整理進度緩慢。對歷史真相的追求,目前為止的成就是民間所做的許多訪談記錄,和國民黨執政時期由官方所推動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4,以及國史館陸續出版的官方檔案。這些努力都為歷史真相的發掘,奠定了基礎的工作。可是令人比較遺憾的是,我們在民主化已過二十年之後仍然未能出版總結政治迫害以及歷史反省的「總結報告」。因為對歷史真相的呈現零碎而散落各地,我們對歷史的反省因此也顯得凌亂而殘缺。5 本文初步地討論歷史記憶中最被忽略、可是對歷史反省卻最為重要的議題:我們為什麼支持獨裁政權、或和獨裁政權合作?
服從或拒絕權威
「永遠不再」(Never Again)是所有新民主國家對過去威權統治的警惕語言。可是如何防止獨裁統治的「永遠不再」?一個比較可行、而且似乎也是唯一可行的方式,是透過對過去錯誤的反省。如果我們的目標是過去所發生的「永遠不再」發生,那麼我們就必須「從最可能深沈的層次上去認知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何發生。」6 同時,也基於這樣的瞭解而對未來保持警戒。「活著就是恐懼,恐懼在許多情況下對我們有莫大的益處,因為這樣的警戒讓我們免於危險。…不止為我們自己恐懼,也為我們的公民同胞而恐懼。」7 自由主義思想家敘卡拉認為,對暴政和殘酷的「恐懼」是自由主義的重要內涵。此種「基於恐懼的自由主義」之基本元素,不是一般自由主義者所提出的反省性的個人,也不是朋友或敵人的差別,而是權者和弱者的對立。權者對弱者的欺壓和殘酷,是自由主義者的最首要的警覺。這是以歷史記憶為基礎的自由主義。而這項重要的歷史記憶,正是洛克、密爾等人的自由主義所缺乏的。8 如果一般缺乏「歷史記憶」的自由主義者只是提供抽象的原則,敘卡拉的「基於恐懼的自由主義」則不止是動態的,同時也提供了重要的行為動力。9 從納粹魔掌中僥倖逃離的敘卡拉,她的想法對我們今天的處境應該有甚大的啟發。可是我們應如何對政治權力保持恐懼、並防止它帶來的殘酷呢?難道僅如敘卡拉所指出的制度上的分權、民間社會的制衡力量、以及財產的保障,就足以防止令人恐懼的政治迫害再度降臨嗎?10
敘卡拉提及「歷史記憶」的重要性,卻未及從民主文化的角度加以申論。民主文化的建立或許是恐懼的自由主義的重要路徑。理解過去的錯誤,以及基於理解而來的反省,或許是防止暴政再度發生的重要機制。如果是,那麼透過何種方式、何種場域,一個社會可以普及地理解過去、並加以反省?理解和反省的一個重要場域,是轉型正義中對加害者的追訴或追究。南非處理轉型正義的原則是,由加害者陳述、交代真相,以換取對其罪行的免訴。加害者交代罪行的兩千多場聽證會,每天都透過電視轉播。這為期兩個多月的聽證會,成為全國人民的靈修場所。而透過面對邪惡的歷史事實、以及面對加害者,全國人民,不論是受害者、加害者、或旁觀者,對邪惡有更深刻的理解,這項理解也刺激著反省。這是建立民主文化最重要的場域。可是,畢竟非常少數的國家有這樣的機會。
甚至起訴全國最高領袖的南韓社會,都不一定獲得此種反省的機會。當全斗煥和盧泰愚穿著囚衣、胸前貼著號碼,站在法官面前接受國家的審判,那確實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場面。可是,它能促成多少反省呢?審判全國最高領袖或許滿足了許多人的正義裡念,可是似乎無助於反省為什麼那麼多人會支持不義的體制。而這項反省正是新興的民主社會所亟需的。
反省、或討論這個重要的問題,鄂蘭的《艾緒曼在耶路薩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以下簡稱EJ) 11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不過卻只是起點,而非終點,也不是全部的故事。艾緒曼是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重要執行者之一;他負責逮捕、運送歐洲的猶太人到集中營。他於1960在阿根廷為以色列的特工所逮捕,立即秘密送回耶路撒冷審判。逃難至美國的德裔猶太哲學家鄂蘭接受美國《紐約客》雜誌委託,前往耶路撒冷旁聽並報導該審判。之後,鄂蘭出版的這本報告書震驚全世界,引起甚多的討論和批評,特別是來自猶太同胞的嚴厲批判。

圖片來源:http://agorataipei.blogspot.tw/,連結請按此。
到底是怎樣一個惡魔,可以冷血地、有計畫地執行屠殺數百萬的人類?這是許多人極想知道的。可是鄂蘭卻回答說,也正如該書書名附標題所宣示的,艾緒曼其實是個最正常不過的人。雖然他積極參與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有組織、最有效率的屠殺,可是他這種邪惡行為的動機其實也是平凡而世俗的。艾緒曼的審判,正如其他所有的政治審判,引發許多法律和道德的問題。例如,根據當時納粹的法律,艾緒曼不但沒有罪,而且還是一個守法的、有效率的官僚。這也是艾緒曼對所有15條起訴他的罪狀都宣稱無罪。他的律師說,「艾緒曼認為他在上帝的面前有罪,可是在法律面前無罪。」(EJ,21) 然而鄂蘭的書引起的最大爭論,還是她對艾緒曼罪行的討論和分析。而該書的附標題、也是核心理念「邪惡的平庸性」,成為20世紀道德哲學最重要的名詞之一。
邪惡是道德哲學最重要的議題。因為對邪惡的理解,牽涉到我們如何理解自己的本質,理解我們可能做出什麼樣的行為。艾緒曼,或納粹,犯下此種「至高的惡」(radical evil) 的動機是什麼?他們是怎樣的人?鄂蘭的回答和一般人的理解明顯衝突。也和康德的哲學對立;惡行並非來自對邪惡信條的有意選擇。鄂蘭認為,如此巨大的惡行並非來自邪惡的動機。正如她後來在寫給她的老師雅斯培的信中所說,「納粹的罪行用任何可以想像的處罰都不夠嚴厲…這種行為的罪惡已經超出任何的法律。」「可是,我們也不應該將這種滔天的可怕罪行加以神秘化。」12 在兩年後的一篇文章中,鄂蘭說道,「此種巨大規模的邪惡行為,並非來自執行者的邪惡、病態、或意識型態信仰。不論這些行為多麼邪惡,行為者絕對不是惡魔。」13
事實上,鄂蘭認為,這個罪行其實非常平凡,而犯下此種巨大惡行的人,也是非常正常的人。他們從頭到尾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崇拜領袖、忠心耿耿地執行法律和領袖的意志。如艾緒曼在法庭中的言論所示,他甚至對康德的道德哲學有非常清楚而正確的了解。(EJ, 24) 他也清楚知道他所作所為是不道德的,可是他更知道:身為優良的公務員,他必須有效率地執行國家的法律,完成領袖交代的任務。因此,艾緒曼並沒有任何悔意;他說,無法分辨善惡的「小孩子才會悔悟。」而他是知道善與惡的分別;他甚至提議自己「在公眾面前上吊自殺,以作為所有反猶太份子的警惕。」(EJ, 24)
雖然可以分辨善惡,艾緒曼卻同時也是一個盡忠職守的官員。一個學歷不高(高中沒有畢業)、汲汲營營為了在官僚體制中升遷而討好上級、力求表現、忠實執行領袖命令的公務員。甚至當艾緒曼在戰爭末期接到他黑衫軍司令希姆萊的命令,要他停止遣送匈牙利的猶太人,他都沒有服從。因為他知道這個命令違反希特勒的旨意。相反的,他發出電報,試圖親自從領袖得到正確的指令。(EJ, 147) 因此,艾緒曼犯下滔天罪惡的動機,其實是「非常的世俗,也非常的人性」14:忠實地執行領袖的意志。
如果艾緒曼所作所為只是人性之常,那麼為什麼有些人不會成為屠殺機器的執行者,有些人卻甘心配合著邪惡的體制、法律、和指令?鄂蘭在書中提到一位暗中援救猶太人的德國仕官,他在持續五個月的救援行動被發覺之後,遭軍隊處決。(EJ, 230) 鄂蘭認為兩者行為的分別是「思考」的能力。鄂蘭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說,「不論是從艾緒曼的過去、他在法庭中的行為、以及他的偵訊紀錄,我們從他身上發現一個完全負面的特徵:不是愚笨,而是令人好奇的、非常真實的思考無能。」15 鄂蘭的洞見和論斷在四十年後似乎被證明為正確。以色列政府在1999年公開了艾緒曼在獄中所寫的1200頁筆記。其中艾緒曼寫道:「對我而言,服從命令是最重要的事。」「我發現:以服從和接受指令為基礎的生活,確實是一個舒適的生活。這種生活讓一個人對思考的需要減到最低。」16 因為沒有能力、或不願思考,一個人雖然有善惡之概念,仍然可以為了個人的工作和升遷、或基於對領袖的效忠,而依法行惡、依令行惡。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鄂蘭用思考和反省怠惰來解釋邪惡,她並不認為人因此就可以免於道德責任。對喜歡用「螺絲釘理論」(cog theory)來辯護惡行的人,說自己只是整個機器中無法自主的零件,鄂蘭質問說:「那你為什麼讓你自己成為螺絲釘,或讓你自己繼續當一個螺絲釘?」17 鄂蘭指出:事實上有許多人拒絕支持邪惡的體制。當他們被要求以服從為名而支持不義命令或體制的時候,他們特意加以閃避。「只要想想看,這種政府會面臨什麼樣情境,如果有足夠的人『不負責任地』拒絕支持它?甚至不需要主動的抵抗和反叛,這種拒絕支持都是一個有效的武器。」18 鄂蘭說得沒有錯,我們看過許多拒絕服從邪惡的體制的例子。南非反種族隔離體制領導人曼得拉第一次受審的時候,白人檢察官在開庭之前,特別去探望曼得拉,對他必須起訴他表示歉意,臨走前並含著眼淚和曼得拉握手。曼得拉的第二次審判更是戲劇性。起訴團中的一位白人檢察官當庭宣布辭職,並且趨前和曼得拉握手道別,然後昂然走出法庭。19
鄂蘭認為這種人雖然不多,可是卻已經足夠刺激我們反省,面對權威除了服從外,我們仍然有其他的選擇。這種人雖然不多,卻已足夠讓我們對人性有新的樂觀;這項樂觀不是來自道德的宣示,而是來自人類在最黑暗時期的表現。
所以,對那些參與邪惡、服從命令的人,我們應該提出的問題不是「你為什麼服從?」而是「你為什麼支持?」如果我們能將「服從」這種破壞性的字眼從政治和道德思想中剔除,我們將大為受益。如果我們能仔細地反省這些問題,我們或許可以重獲自信、甚至重獲驕傲,亦即重新獲得以前我們稱之為人的尊嚴、或人的榮耀的東西:也就是生而為人的地位。20
也就是說,在鄂蘭對邪惡世界的理解中,邪惡行為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為平凡人對權威的盲目服從。要遠離邪惡,人必須學習拒絕權威。而人也不能因為用「服從權威」來規避道德責任。鄂蘭的邪惡和救贖理論,以對權威的服從和拒絕為核心。人內心的空洞、膚淺、沒有思考能力。在旁聽審判之後兩年所寫的一篇文章「思考與道德思慮」中,鄂蘭總結她的想法:
在報導艾緒曼審判的時候,我提出「邪惡的庸常」之概念。它並不是一個理論或教條,而只是一個事實:這種巨大規模的邪惡行為之來源,並不是行為者的惡劣、病態、或意識型態;他們性格唯一的特徵或許只是其心超越常人的空洞。不論這些行為是如何地像惡魔,行為者絕不是妖魔。而我們從其角色和行為中可以偵測到的特徵,並不是愚昧,而是一種令人好奇的、非常真實的思考無能。」21
可是執行邪惡指令的人,只是單純地在服從權威嗎?他們真的是內心空洞的人嗎?還是:他們的內心其實充滿了意識型態,也因此讓他們成為積極樂意的執行者?
結語:只是因為服從?
《艾緒曼在耶路薩冷》出版後,立即引起熱烈的迴響。其中有讚美,也有批評和攻擊。至目前為止,超過兩百本著作和論文討論鄂蘭的理論。鄂蘭的著作也成為政治哲學討論邪惡和權威必讀的作品。耶魯心理學家密爾綸(Stanley Milgram)著名的電擊實驗,也以相同的理論視野為指引。在該實驗中,招募來的平凡人負責控制電擊按鈕;實驗助理則充當被電擊的人。每當助理答錯問題,主持實驗的教授就命令平凡的志願者施以電擊,而且電流愈來愈強。電擊當然是假的,助理痛苦的表情也是偽裝的。令人驚異的是,即使當志願者被告知電流已經達到致命的強度,許多人仍然接受權威繼續執行教授的命令。密爾綸的實驗並非受到鄂蘭的影響;他的實驗於1960年開始,那時艾緒曼的審判剛開始數個月,鄂蘭的書則要三年後才出版。密爾綸在其研究報告中認為,他的實驗支持了鄂蘭的論點:「一般的平凡人,即使不懷任何敵意,而僅是從事他們被指定的工作,就可能做出恐怖的毀滅性行為。甚至,當他們發現行為的毀滅性後果之後,很少人會抗拒權威、停止執行不合乎其基本道德理念的行為。」22
可是類似艾緒曼這種的恐怖劊子手,他們本身真的沒有任何意識型態,其邪惡行為只是來自對權威的服從嗎?二十世紀是人類史上最殘酷的時代。眾多執行殘酷虐殺同胞的人,不論是在德國、蘇聯、中國、西班牙、拉丁美洲、柬埔寨、南非、蘇丹、賽維亞、或較小規模的台灣等,他們只是在執行命令嗎?鄂蘭的解釋似乎過於單面向,而且也不盡符合歷史事實。
經過數十年的關心和探究,如今我們知道艾緒曼真正的為人。他決不是如鄂蘭所說,內心空白、絕對服從指令的人。鄂蘭等人對艾緒曼人格的錯誤理解,以及因該理解而導致的片面理論,其實都來自艾緒曼的特意操弄及掩飾:包括法庭上的辯護策略、以及對死後聲名的維護。艾緒曼從一開始,就以「道德上有罪,法律上無罪」為辯護策略。在法庭上他不斷強調,他絕對不是一個仇恨猶太人的人,他的所作所為都是執行當時德國的法令;雖然他也同時強調,他所執行的命令確實是一個道德上的巨大罪過。如果他的說詞被接受,確實會對定罪造成困境:將他定罪等於承認、或鼓勵任何個人,都有權利反抗任何他認為不合理的法令。以色列法庭當然不接受他的說詞;整個審判本就充滿政治目的。可是很多學者接受他的說詞,因為即將死亡的人何必說謊呢?
艾緒曼為何要說謊?因為他非常在意死後的名聲,以及對他家人的影響。事實上早於1951年在阿根廷,他就開始雇用秘書以錄音撰寫回憶錄,並親自仔細修改逐字稿,希望死後出版。艾緒曼於1957年在阿根廷第二度接受錄音訪問,訪問者是前黑衫軍軍官。這份厚達七百多頁的訪問稿,同樣經過艾緒曼親手仔細修訂。這些文獻都顯示出艾緒曼對死後名聲的在意。他在審判期間寫給他律師的信中清楚顯示了這樣的心情。「我關心的是,我的孩子、他們的孩子、以及更後面的孩子們都能閱讀它們[審判的文件],以便知道他們的父親、祖父、以及曾祖父絕不是一個謀殺者。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是這件事,而不是倖存下來。」23
可是事實上,艾緒曼是一個對猶太人充滿仇恨的人。而仇恨猶太人卻是當時德國普遍瀰漫的意識型態。24 他曾經對友人表示,對於未能解決徹底消滅猶太人的一些障礙,他感到懊惱。「我坦白告訴你,我們現在知道統計學者柯賀估計,猶太人總共有一千零三十萬人,如果我們消滅了一千零三十萬猶太人,那我會非常滿意。我會說:『好了,我們終於完全消滅敵人了。』」25 在大戰期間,有朋友問艾緒曼說,如果德國戰敗他會有什麼遭遇?艾緒曼回答說,「我會很高興地跳進墳墓,因為至少我成功地屠殺了五十萬猶太人。這給我很大的滿足和光榮。」26 有這樣的父親,艾緒曼的兒子難以避免地也充滿了反猶太的意識型態。事實上,也是他兒子不小心透露出反猶太思想,而導致艾緒曼的被捕。他兒子有一次到女朋友家作客的時候,不小心說出「如果德國成功地滅絕猶太人就好了。」因為女友的父親知道這位年輕人的父親曾經是德國納粹的軍人,因此產生了懷疑,而將之舉發。雖然經過數年的忽略和拖延,最終還是導致艾緒曼為以色列特工所逮捕。27 艾緒曼因此絕非只是一個內心空白的服從者。相反的,他和當時的許多德國人一樣,內心充滿了對猶太人的仇恨。
這種對猶太人的強烈仇恨,讓當時許多德國人並不特別需要權威的指令,就可以做出殘酷的行為。事實上,納粹政權在許多情況下都容許它的軍人有選擇的自由。因為道德或心理因素而無法執行屠殺任務而請調的軍人,通常都不會受到懲罰。惡名昭彰的警察101營在執行第一次的屠殺任務之前,營長在隊伍之前公開宣佈:無法執行屠殺任務的人可以毫無負擔地免除這項工作。根據士兵在事後的回憶,當場的氣氛完全沒有脅迫性或社會壓力。可是在將近五百人的隊伍中,仍然只有10到12個人表示不願意執行屠殺任務。28 而這並不是特例。一位研究納粹大屠殺的學者伯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指出,「在過去四十五年間審判戰犯的數百個案件中,不論是受審人或其律師都無法舉出任何一個,因為拒絕接受殘殺平民的指令而受到懲罰的例子。」
因政治權威而來的邪惡,是政治學最重要的議題之一。雖然鄂蘭的解釋過於片面,而她對艾緒曼的解釋則是錯誤的。可是她所提出問題、以及提供的解答,仍然是我們研究這個重大議題的起步。
如今我們已經知道,第一,加害者(或協力者)是由許多不同種類的人所組成。除了如艾緒曼般的狂熱反猶太份子外,也有基於專業精神的執行者,29 也有在無任何指令下即仰承領袖意旨自動自發的屠殺者,30 甚至有介於執行者和反抗者之間的人。31 在壓迫體制中,必然也存在著只是被動接受指令的執行者。
第二,在很多情況中,服從權威確實讓人做出違反自己道德理念的行為。密爾綸在其研究報告中用越戰時期非常轟動的美來村事件為例子,來支持他的實驗結論:美軍士兵接受軍官指令,以機關槍和手榴彈屠殺了一百七十多位平民,其中包括婦女、小孩、和嬰兒。32。鄂蘭對邪惡的分析主要集中於政治和社會學的層次,忽略了更深層、更複雜的人性。她的分析因此被批評為「單面向」,好比經濟學者對愛情的分析。33 可是,也正是這樣的社會學和政治學分析,特別值得成為我們思考問題的起點。因為台灣的政治迫害非常的官僚化。除了二二八事件期間和隨後的階段,以及其他的少數案件(如江南案、林宅血案),台灣的政治迫害多由官僚化的情治、軍事機構和人員負責執行逮捕、審判、和監禁。我們需要反省的乃是:我為什麼參與,或以鄂蘭的話,為什麼支持這樣的體制?
侵犯人權的執行者和行動,來自不同的權力階級、機構歸屬、和行動方式。有發號施令的,有接受指令而執行的。有身處執行機構的,如警備總部和調查局;也有身處其他的政權輔助機構的,如行政體系、教育機構、和媒體。行動方式有依法令而執行的,如逮捕、判決、監禁;也有超越法律的,如陳文成案、江南案、和林家血案的政治謀殺。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機構、和不同的行動方式,應有不同的道德責任和反省角度。
可是至目前為止,不論掌握何種權力位階,不論身處何種機構,我們對這項重大的問題一直沒有反省。由於政治迫害官僚化的本質,除了少數政治謀殺例子之外,我們或許不用對其中的「公務員」做法律的追究。可是為了「讓未來不再」,全社會對它的反省卻是必要的,反省我們為了個人的方便、個人的工作、個人的政治生涯,支持、配合迫害人權的政權。
反省的結果不一定是承擔確定的道德責任,特別是某些不論是生活上或職務上都別無選擇的低層公務員。如果我們回顧那個時代,許多追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公務員,在生活上確實沒有太大的選擇。而在職務上是否有自由選擇、或消極不配合的空間,我們仍不知道,因為我們沒有經過反省運動。可是許多政務官確實有自由選擇的空間。而正如鄂蘭所說的,不需要公開的抵抗,只要消極的不配合就能產生巨大的影響。1985年雷根政府因為政府內部洩密連連,計畫對所有的聯邦公務員進行強迫性的測謊。當時的國務卿舒茲雖然以團隊精神而著名,卻公開表示將不惜辭職抗議。結果是雷根總統收回的既定的計畫。34
正因為我們沒有經過反省運動,所以我們的社會仍然是非不分。陳聰明檢察官在威權時期曾經根據選舉文宣起訴民主運動人士,不同的新民主國家在追求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對此類迫害體制的協力者或執行者,或有不同的處置方式,如法律的追究、或公職的禁止、或道德的追訴,可是很少如台灣這樣,為民進黨政府任命為政府統帥全國檢察官的人。35 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沒有經過全面性的反省運動。也正因為我們沒有經過反省運動,我們仍然盲目支持、甚至效忠自己陣營的領袖,不論是基於個人的意識型態,或基於個人的政治生涯之所需。我們對仇視不同陣營的政治領袖也視為理所當然。我們對這些態度都毫無警覺心,沒有警覺它們正是培養獨裁政治、讓獨裁政治得以順利運作的文化精神。盲目服從權威並不是壓迫體制的執行者唯一的行為動機。可是我們知道,執行者由各種不同思想、不同背景、不同專業的人所組成。對權威的服從是其中部分人配合壓迫體制的動機之一,也是卻為壓迫體制可以順利運作的重要條件之一。
註1. 〈服從權威是邪惡的根源嗎?*〉標題註解*,內容為:本文發表於「解嚴二十年之回顧與前瞻研討會」,台北律師公會、思與言雜誌社等主辦,台北市,2007年12月9日。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所提供的意見,也根據部分意見做了適度的修改和大幅度的增加。錯誤和疏忽當然是我自己的責任。摘錄自吳乃德,2009,〈服從權威是邪惡的根源嗎?〉,《思與言》,第47卷第3期,頁1-25。
註2. 菜市場政治學轉型正義延伸閱讀
- Jurgen Habermas and Adam Michnik, “Overcoming the Past,” The New Left Review No. 203(1994):13-14。 ↩
- 對台灣處理轉型正義更詳細的討論,參見吳乃德,「轉型正義和歷史正義: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思想》第2期(2006, 6):1-34。 ↩
- 上引文,21-23。 ↩
- 賴澤涵等,《「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1994。 ↩
- 一個例子是今年「二二八事件補償基金會」在出版張炎憲等,《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台北:二二八基金會,2006)後,在社會所引起的兩極化反應。對各政治陣營的二二八事件論述的初步討論,參見吳乃德,「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論述」,《思想》第8期(2008, 1月):39-70。 ↩
- Robert I. Rotberg, “Truth Commissions and the Provision of Truth,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ed. R. I. Rotberg and Dennis Thompson, Truth V. Justice: the Morality of Truth Commiss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 Judith Shklar, “Liberalism of Fear,” ed. Nancy L. Rosenblum, Liberalism and the Moral Lif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9。 ↩
- 上文,27。 ↩
- John Dunn, “Hope over Fear: Judith Shklar as Political Educator,” ed. Bernard Yack, Liberalism without Illusions: Essays on Liber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Vision of Judith Shkl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 上文,30-31。 ↩
-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Penguin, 1963. ↩
- Richard J. Bernstein, Radical Evil: a Philosophical Interroga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2), 214-15。 ↩
- Hannah Arendt, “Thinking and Moral Considerations,” in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3), 17。 ↩
- Bernstein, Radical Evil, 220。 ↩
- Arendt, “Thinking and Moral Considerations,” 159。 ↩
- The New York Times 1999/8/15。 ↩
- Hannah Arendt,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Dictatorship,” in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31。 ↩
- 上文,47。 ↩
- Tom Lodge, Mandela: a Critical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5。 ↩
- Arendt,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Dictatorship,” 48。 ↩
- H. Arendt, “Thinking and Moral Considerations,” in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3), 159. ↩
- 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London: Tavistock, 1974), 6. ↩
- Christian Gerlach, “The Eichmann Interrogations in Holocaust Historiography,”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5, 3(2001), 432-33. ↩
- 德國普遍的反猶太意識型態,參見Daniel Jonah Goldhagen, Hitler’s Wil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7). ↩
- David Cesarani, Becoming Eichmann: Rethinking the Life, Crimes, and Trial of a “Desk Murder” (Cambridge, MA: Da Capo Press, 2007), 219. ↩
- Michael Mann,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45. ↩
- Cesarani, Becoming Eichmann, 221. ↩
-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211-13. ↩
- Martin Jungius and Wolfgang Seibel在 “The Citizen as Perpetrator: Kurt Blanke and Aryanization in France”一文中報導了此種類型中的案例:沒有反猶太意識型態的專業律師,在法國執行處分猶太人財產的工作中,將其專業發揮到極致。可是,兩位作者並沒有清楚說明,為何這位律師沒有反猶太意識型態。雖然我們不否認有這種類型的存在,可是這位律師是否屬於其中之一,我們暫時存疑。 ↩
- 1941年一個由37人組成的黑衫軍排於調往東歐駐紮的途中,在沒有任何指令下,將沿途所經的波蘭、烏克蘭城鎮中的猶太人集體屠殺。這三十多個軍人大約屠殺了數千猶太人。排長Max Taubner喜歡的屠殺方式是:將小孩從父母懷中搶走,抓住小孩的頭髮將他們提到半空,然後在父母面前用手槍朝小孩的頭顱射擊。他們的屠殺行為因士兵們將照片給親友們傳閱取樂而敗露,引起黑衫軍總部的注意。雖然他們的屠殺行為非出於指令,可是卻是主動執行領袖的旨意,因此對審判造成了困擾。結果軍事法庭在黑衫軍頭目希姆萊的介入下,將排長判刑兩年。Yehoshua R. Buchler, “’Unworthy Behavior’: the Case of SS Officer Max Taubner,”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7, 3(2003):409-429. ↩
- Valerie Hebert, “Disguised Resistance? The Story of Kurt Gerstein,” 討論了一個這樣的特殊案例:曾經因反對納粹的政策而被逮捕,卻自動申請加入黑衫軍,希望「從內部反抗」納粹。他的工作是負責訂購及運送毒氣瓦斯到集中營;可是不但在運送中途故意破壞,也努力將集中營的真實情況傳到西方世界,希望能阻止大屠殺。戰後他主動向法國軍隊自首,卻不為法國軍隊採信,因而而在獄中自殺。戰後因為其遺孀申請退伍軍人補助而和德國政府及法院纏訟數年,希望能確定他不是加害者,而是反抗者。雖然德國法院最終仍然沒有更改他加害者的身份,他的朋友、甚至集中營的倖存者都出面支持其反抗行為。 ↩
-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183-89. ↩
- Paul W. Kahn, Out of Eden: Adam and Eve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 ↩
- 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 Ethics and Politics: Cases and Studies 4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2006), 211-17。 ↩
- 陳聰明於1981年根據民主運動人士劉峰松於競選期間的標語「長期戒嚴,扼殺民主;萬年國會,踐踏民權」等事實,以「煽惑他人犯內亂罪」之罪名將之起訴,導致劉豐松被判刑三年六個月。參見劉峰松,《選舉官司》(作者出版,1981),103-07。陳聰明於2006年獲陳水扁總統任命為最高檢察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