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偉傑/美國羅格斯大學地理學博士生
書目:《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
作者:徐世榮/作,張雅綿/整理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日期:2016/09/28
※本文原由風傳媒刊登,經作者及該網站同意轉載。
※廖彥豪、洪偉傑、詹竣傑三人的書評及勘誤目錄及檔案列表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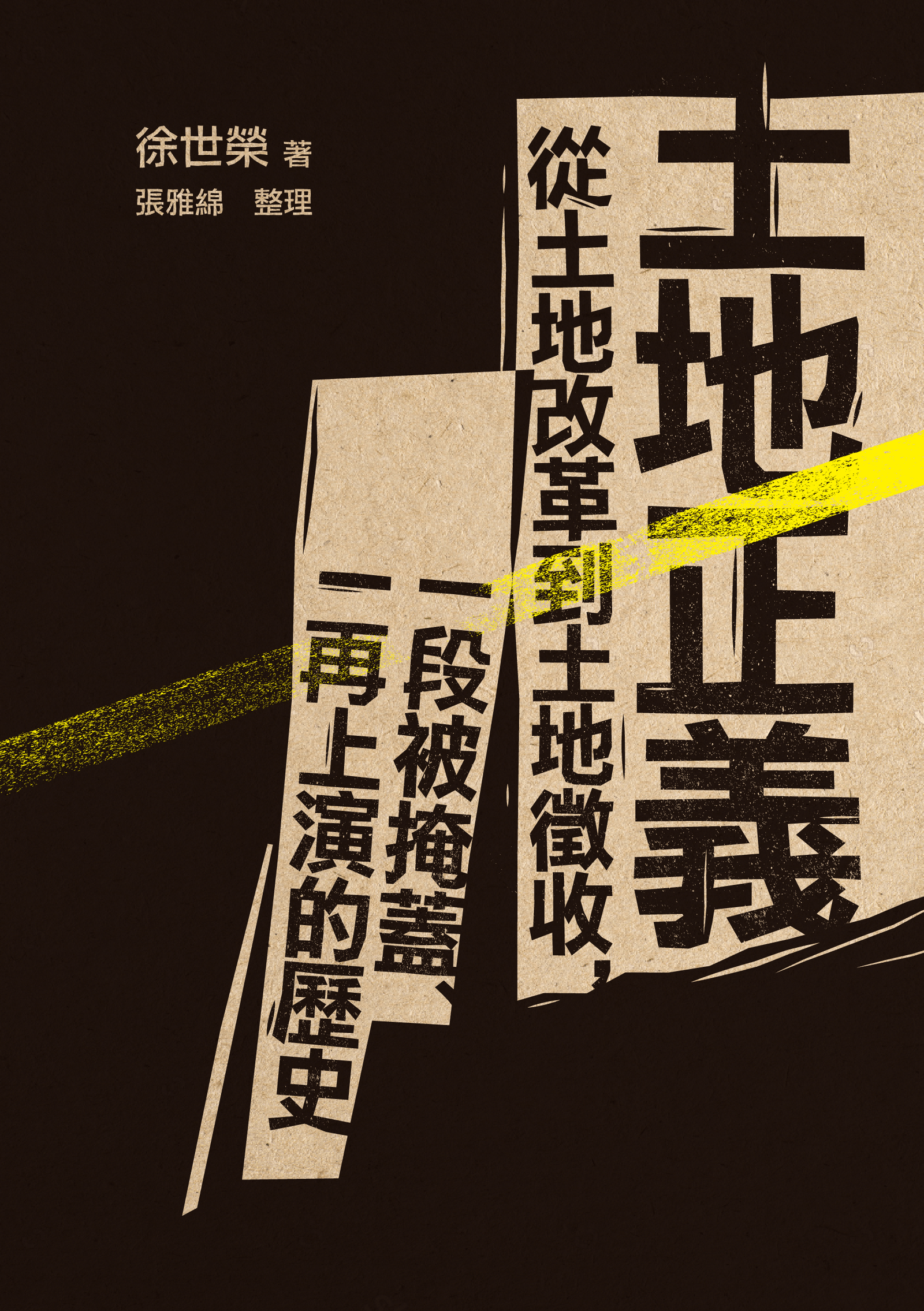
圖片:書本封面。
本系列兩篇關於徐世榮教授《土地正義》(2016)的書評,緣起於廖彥豪受邀評論此書,廖再邀請詹竣傑跟我一同貢獻評論,希望從不同的視角,對這本受台灣學界與社運圈矚目──特別是土地與空間相關社群──但卻不無爭議的大眾書寫,檢視其內容及對相關議題的影響。三人協議分工後,由廖評論徐書上篇的土地改革再檢討,並提出徐書內容之勘誤表,詹評論下篇關於當前土地徵收爭議的反省,我則為兩篇評論撰寫導言,簡介兩篇書評作為閱讀指南,並提出整合兩篇文章的觀點。
這兩篇書評看似分工清楚地將《土地正義》一書拆成上篇與下篇進行評論,但是不管是《土地正義》本身,或是這兩篇書評,都不是分割清楚的「歷史」與「當下」兩部。在徐世榮教授的論述當中,他將「國家-社會」關係的過去與現在相連,指出一個具高度宰制力的政權,從戰後延續至今,恣意剝奪弱勢人民的土地。廖與詹的書評同意台灣的土地議題具有歷史的延續性,但是不同意「威權體制」是貫穿其中的邏輯。兩人分別從制度改革史的文獻考據以及運動改革的參與經驗指出,儘管土改的歷史確實型塑了台灣當前的土地問題,但是不論是從權力關係的分析,或是從人與土地的關係,都不是徐所主張的(威權)國家宰制(弱勢)人民、人民對土地/家園的情感被貪婪的政權所傷害、轉化為少數菁英壟斷的土地資本。
解構「黨國/威權」:簡化的「國家/人民」二元對立
本系列書評的第一個重點是針對簡化的「黨國一體」與「威權國家」,廖彥豪拆解了土改推動過程中,「黨」與「政」、「中央」與「地方(省、縣市)」、「行政」與「立法」等不同行動者的角色,並指出人民──徐所稱可憐的地主──如何參與到政策的形構過程中。廖彥豪並未否定「弱勢人民」的存在,但是關於誰是弱勢人民、誰讓弱勢人民成為不同政策行動者協商後的犧牲對象,廖藉由分析「共有地」徵收的決策過程,描繪出一個更清楚的圖像,並指出徐的「最小抵抗原則」說(二二八事件後本土地主菁英受到很大打擊,因此無法抵抗政府的決策),僅追究政府與技術官僚的責任,而忽視本省地主菁英的共謀角色(2017)。廖彥豪分別從(一)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草擬與協商過程、(二)「和諧業佃關係」背後真實的權力關係、(三)共有地的地主組成與徵收的博弈過程,三個方面,指出《土地正義》對土改過程與其間權力關係運作的錯誤理解。以共有地徵收為例,廖彥豪指出,徐世榮對耕者有其田研究的實質貢獻,在於指出部分弱勢共有小地主成為土改犧牲者的事實。然而,廖彥豪進一步指出:第一,共有地小地主不是一個同質的群體,有純出租的共有小地主,也有家族共有、兼有出租地與自耕地的中大地主;第二,共有地成為最後政府徵收主體的關鍵有二,其一是國府為達耕者有其田的徵收目標,共有地與個人和團體有耕地之間形成競合關係,其二則是共有小地主請願、獲立院黨籍外省精英支持,但是卻在前述的競合過程中,成為國府與本省地主菁英協商後的犧牲對象。透過這些過程,廖彥豪的核心論點在於,本省地主菁英透過省府與議會系統,其實相當程度改變了原先國府技術官僚的改革方案,最後決定哪一個類別應該多徵收(共有地)、哪一個類別應該給與地主保留或進行有限度徵收(個人有),雖然看似是政府單方面的決定(甚至是蔣主席的裁示),但是廖認為,不能忽視中大地主為主體的本省菁英在其中鬥爭與共謀的角色。
而詹竣傑則從過去數年來參與住宅與都市計劃改革運動的經驗,試圖描繪社會運動、改革倡議實際遭遇的困境與背後的權力僵局。為什麼高房價、都更與徵收迫遷、容積獎勵與移轉浮濫、工業宅/農舍/農地工廠等土地住宅問題層出不窮?為什麼儘管人民對此深惡痛絕已久,但是問題卻沒有好轉的跡象?詹認為,原因不是因為我們罵國家罵的不夠兇,所以霸佔國家機器的政商聯盟可以繼續胡作非為,而是人民也顧慮改革是否會讓他們的產權夢、都更夢破滅,因而消極保留,或是積極反對。廖與詹對權力關係的分析,共同回應了當前社會運動與制度改革的困境:持續複製「譴責國家暴力、有權有勢者貪污勾結炒地」的這套論述,以及這種手指他人的邏輯,究竟在什麼意義上對結構性的改革有效?或者只是不願意承認土地產權共犯集團你我都參了一腳的幌子?

圖片來源:台灣農村陣線。
「產權-家園」論述:找回空間的公共性
本系列書評的第二個重點是對訴諸「基於產權」的「家園情感」提出直接的質疑。徐世榮教授認為,對於土地、家園的情感是人們反對政府徵收土地的核心,認為徵收是種對情感的剝奪。然而,廖質疑這種主張在實際徵收案例中的普遍性。廖引用既有研究中地主對土改的評價(包括徐過去的研究),主張「增值獲利不均」造成的相對剝奪感,恐怕比起家園情感更能解釋多數地主對土改的不滿。廖更進一步針對徐「解除三七五租約」的主張,質疑徐所捍衛的土地情感,弔詭地建基於所有權體制之上,既非土地使用者(佃農)與土地相依存的情感,更不是土地之於社會的政策意涵(如糧食政策與農業發展)。廖認為,徐所批判的土地掠奪,正是建立在產權優先性之上,透過土地利益歸私的分配體制與政治參與機制,鞏固了當下的產權體制,並且轉化了人與土地的關係。詹則是舉近期反對社會住宅的鄰避運動(Not in my back yard, NIMBY)為例,指出產權至上論與家園情感的結合,使得公共政策難以被討論。詹認為,這個「產權-家園」論述的核心問題在於,以家園情感動員社會中的個體對於失去家園的恐懼,一方面強化了以所有權為邊界的土地社會關係(有產權才有人權),使人們退縮到當下產權體制中的位置,拒絕正視土地不正義的根源與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使個體更加分散化,甚至我們可以在都更與徵收議題中,看到家族成員產生糾紛,即使存在「家」的情感,也是會被分化。對此,廖與詹的書評都對《土地正義》落入產權至上的陷阱有相當大的批評:即使政府在很多意義上並沒有把徵收的公共性、必要性討論清楚,而需要被挑戰與進一步的社會辯論,但是在什麼意義上,透過鎖定「國家」作為以及鞏固了「產權-家園」的論述,是一個真正進步的改革方向?
廖與詹的文章,雖然並未提供一個按部就班就可達成的改革/運動教戰守則,但是這兩篇對於《土地正義》的反響,應可開啟我們對當下土地問題困境的重新理解。具體來說,了解土改推動過程中,黨政體系推動土改的目的與政治意志、地主菁英如何透過民意代表體系影響省府與行政院的草案擬定、真正弱勢的共有地小地主如何在協商過程中被犧牲,是否有可能幫助我們思考如何突破當下制度改革的困境?不管是關於都市更新與容積管制、農地管制與農舍問題、閒置房地釋出(農地、工業區、以及城市空餘屋)、違章建築、房產稅制的改革等各種土地/空間議題,值得思考的是:其中的關係人、利益團體、政府角色為何?面對潛在的改革方案,各方的顧慮與考量是什麼?誰是最弱勢、最可能被邊緣化、被犧牲的群體?當下的土地產權結構固然可以被批判地理解為一個共謀得利的體系,但另一方面,當一般大眾問為什麼房價如此高、換屋多麼不容易、公共設施不足、環境污染與空間使用不均時,這個土地產權體系確實也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共同受害。除了家園論述,運動者是否有其他的動員策略鼓勵人們走出產權框架、探索土地與空間的集體面向,以及更包容但也更負責的空間想像與實踐方案?

圖片來源:C.C. by todei
土地問題的轉型正義如何可能?
最後,關於徐世榮教授提出土地議題也需要「轉型正義」的看法,個人認為是具啟發性的提議。然而,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中,轉型正義最困難的部份,往往不是對顯而易見的戰犯判刑。1最難的,是發現那些長久以來與我們一同生活的最親近的家人、朋友,其實是加害者的共犯。2在這種情況下,當人們揭露真相之後,要如何回到真實生活中與那些最親密的共犯相處、渡過每一天?如果台灣的土地議題也需要納入轉型正義,不管是土地歷史資料的清理與公開、追究體制或個人責任、針對受害者的象徵與實質賠償、以及最重要的──改革不正義的制度,終止不正義的再次發生,這些都需要更多的社會溝通,以及不同個人、群體對自身在不義體制中的獲利與共謀進行反省,探討如何修正當下的體制,辯論、探討社群的未來。如果我們將責任完全推給「威權國家」或「少數政策制定者、有權者」,也許是個輕快無負擔的做法,但也無法面對體制問題,進而生產更多不正義的緣由。
《土地正義》一書反映的是台灣社會對當前土地問題及其歷史形成因素的典型理解方式,詹與廖的書評所提出的批判也許尖銳,但是我們希望這是開啟對話與具建設性辯論的起點,目的是反省、改革當下的產權體制,而非對歷史的拍板定案。
※本文作者聯絡方式: weichieh.hung@rutgers.edu

如何為土地定價?選讀《土地正義》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029-culture-book-landjustice/
佩服各位對於土地正義的論述,所呈現的對話和辯證也發人深省。然而有關土地正義論述的主軸,局限在「致害者」與「受害者」的二元的思辨中,是否真正能夠切中問題核心?是否因為掌握到致害者,排除致害者而使得這個社會回歸正義?「致害者」與「受害者」是兩種不同的社會族群?還是其實是一體的兩面?我認為更寬闊的討論時需要的,特別是回歸整體社會結構的關照,或許能夠讓我們更清楚的看到我們必須思考解決的癥結。
一個都市化時代,土地正義顯然必須回到都市發展中土地被需求和交換的脈絡來檢討,談土地,就必須扣連著房地產一起談。土地和房地產是否是自由商品?還是一種必須被限制的公共財?亦或是必須在自由化與社會化兩極對偶中被高度動態政治「介入與調節」的社會財?這種思維,顯然呈現了土地正義必須被關照的另一組光譜,我認為也是土地以及空間公共性的核心關鍵。
房地產基本上是都市發展中的一種關鍵的動力。在台灣的嚴重性表現在都市發展被房地產狂飆綁架的困境上。這種魔咒現象的形成,在於政府在80年代開始放任房地產(還有股票)成為自由商品,賦予了房地產在社會財富積累過程中巨大的移轉能力,社會上透過土地與房地產追求社會財富的積累,成為一種狂飆的全民運動。這種經驗,或許是我們更需要去面對的。
在近代社會都市發展中,世界各國對房地產的態度是非常愛恨交織的!房地產是諸多內需產業的火車頭,在帶動社會成長上,是被期待的。然而房地產作為社會財富轉換的載體,卻是被壓抑的,因為房地產所依賴的土地資源,一方面是一種稀有的社會財,另一方面其價格結構的形成,基本上不是個人努力的結果,而是都市整體發展的需求,是透過都市計劃為手段,人為的設定和控制而構成(這就是國父所推動漲價歸公的道理)。再者房地產作為一種商品,不是一種在消費、生產、交換過程完全自由的商品,這將導致社會不同族群無法公平進入市場,無法完全自由消費的可能性。這種經驗進而形成社會財富分配的差異和扭曲,也導致社會貧富的兩極化對立。世界先進國家在都市發展中對房地產的控制極嚴,透過各種住宅政策,一方面必須確保房地產作為社會火車頭的動力,卻又要防範社會財富扭曲所導致的社會對立,除了各種多元而複雜細膩之社會補貼和房價控制的政策外,避免房地產成為社會財富不當轉換的載體。其中,除了節度私有資本透過土地與房地產獲利的能力外,政府制度性的全面放棄透過公有土地買賣作為政府稅收的載體,幾乎是一個好的都市與社會政策的基礎。房地產狂飆,代表著政府在房地產發展的社會控制上的失守。在台灣,而這種制度性結構性破壞的始作俑者,就是政府的制度本身(而且不管是哪一個政權的政府,都一樣)。
1987年政府帶頭在都市發展遇到危機的時候,公開拋售公有土地,在完全未考量社會公益性,都市發展的整體效益性前提下,以政府稅收的合法性為掩護,不顧房地產炒作可能帶來的負面社會效益,追求土地價格的最大化。這種政府自己帶動房地產炒作的行動,擴延到所有握有大量公有土地資源的政府機構,包括國防部、國營事業等單位等。這種販賣公有土地資源的行動到現在都還是政府制度上,認為是改善政府財政的主軸,2014年位於台北都市中心地帶的空軍總部,也是以追求房地產最大利益為訴求。政府高價土地的釋出,不但帶動周邊私有土地的炒作和上漲,所販售的土地也因為高價,變成有錢人追逐的商品,更進一步破壞扭曲了社會結構的穩定。
政府制度性帶頭炒土地的另外一個動力,來自於政府對於區域均衡發展政策的失守。1986年政府推動縣市綜合發展計劃,一方面企圖彌補政府在區域均衡發展表現無力的窘境,另一方面也在地方自治上給與地方派系和勢力發揮的空間。關鍵在於地方綜合發展計劃的內容中,並沒有給與地方任何經濟發展的權限,更沒有在稅收制度上設計,導引地方進行有意義的發展。縣市綜合發展計劃因此成為地方爭取公共設施畫大餅的計畫,地方剩下能表現的,也只剩下都市的發展,透過房地產的推動來爭取僅剩屬於地方的稅收(土增稅和房屋稅)。這種行動導致了地方即便在人口沒有成長、經濟不斷往下衰退的情形下,依舊推動都市的擴張和房地產的發展。房地產運動因此成為台灣的全民運動,這個運動更深入民心,成為社會發展指標的共識。
土地正義的探索,如果不面對這種魔咒,將土地和房地產是作為共有財或私有財的社會辯證中,重新被釐清,重新調整我的社會制度性結構與機制,將魔咒背後的社會張力解除,我們又如何能夠期待正義的到來??
我認為轉型啟動的第一步行動並不難,關鍵就在於解除魔咒:解除土地被賦予社會價值不當轉移能力的魔咒。第一個步驟,政府首先放棄任何發展行動中,公有土地作價的財政制度性糾結(無論是政府公部門、軍方、國營企業等)。公有土地的投出只能在社會公益的地方的效益上作主張。第二個步驟,解除地方政府透過土地追求地方發展的張力,引導回到經濟活動的打造與建構。具體做法,是改變地方賦稅結構,增加地方營業稅、貨物稅與所得稅留在地方的比例,改變和降低土地相關稅收成為地方主要稅基的扭曲性結構。當地方稅收進帳的方式被改變,透過土地尋求發展的張力自然降低。第三步驟,透過綜合政策與財稅手段,調節房地產的獲利機制,引導讓房地產投資獲利的機會,等同或低於對其他社會產業的投資獲利機會。當追求其他產業投資獲利機會,大於房地產時,聰明的社會民眾就不會形成全民焦慮運動,唯房地產是圖。第四步驟,透過社會透明過程,強化土地取得社會成本的計算,特別是地方承載性與社會問責性的價格化。這兩種機制的設定,不只是保護社會弱勢,而是引導地方追求發展時,真正成本的計算,進而引導地方邁向聰明發展與成長的模式。
當土地透過社會政治與綜合手段的調節,不再具有不當財富轉移的能力時,或許我們就有機會可以談土地正義的議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