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美/中研院社會所
本文為商周出版《叛離、抗議與忠誠》一書導讀
如果要在二十世紀(甚至直到今日)選出一本厚度最薄卻最有份量的社會科學著作,《叛離、抗議與忠誠》堪稱第一。本書作者赫緒曼曾經提及,有關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專書被寫出來,通常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作者在尚未撰寫以前,已經找到答案或精彩論題,至少確定是啟發性的見解;另一種是,作者對問題沒有答案,但想要找到答案的憂戚之心,只有透過書寫才能提供。前一種寫作契機幫助作者把心思聚焦在答案,會以為自己的答案不只可以解決一個問題,而是很多問題;後一種寫作動機從問題出發,引導惶惶困惑之心尋找的不只一個答案,而是多種答案1。
赫緒曼的著作,多在第二種分類下寫出來。這樣的寫作動力,讓他對問題的求索具有深沉關懷,卻不至陷入悲觀。畢竟,解決問題的答案不只一個,而是有很多可能性。讀者常從赫緒曼看事情的角度發現,被他命名的一些概念,如本書的「叛離」(轉向支持另一機構、產品或信仰)與「抗議」(對現狀提出意見、批評和反對),非常靈動。赫緒曼透過概念的雙向流動,把人與組織的複雜關係聯繫起來,也在其他層面展開,形成一系列不斷擴大的組合反應。
本書的卓越在於,用簡單易懂的詞彙,表達基本和可見的反應,不管透過「叛離、退出、拋棄」或「抗議、表達、批評」,都在捕捉人們糾結於離開或留下之間的反覆——應該退出遠走?還是就地發聲?什麼時候需要在兩者之間切換抉擇?
由於現實世界的選擇並不明確,赫緒曼也透過心理學和社會心理的解析,進一步釐清人與社會的糾葛面貌,做為了解人們選擇的輔助;而「叛離」與「抗議」則分別指向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分野,這兩種面對事情的回應,既可混合替換,之間也不互斥。 簡言之,人們很少是頑固的叛離者或純粹的抗議者,有時相互替代,有時採取互補,有時彼此破壞,其中牽涉的是混合與轉換的煉金術。
在赫緒曼的筆下,這本關於幾個簡潔行動概念的書,立刻變得複雜起來。在此提幾個書中闡述為例。比如,從消費者對紅酒、乳酪或小孩教育品質要求的不同,赫緒曼說明,當這些「產品」的品質下降,將帶給不同顧客群不同經濟損失的主觀評估。 就行家紅酒顧客而言,他們的消費者剩餘比較多,願意花費高價購買某一個品牌紅酒,一旦紅酒品質下降,會立刻選擇叛離,因為有其他品牌可以替代。也就是,消費者剩餘比較多的人,選擇叛離的機會比較大。再者,「抗議的力道」則可被需求品質的彈性所決定,當產品品質下降,消費者首先想到的是,要不要叛離換個產品?而不是去影響企業產品的品質。只有消費者決定不換品牌,才比較可能出面抗議品質的低落。赫緒曼問:「在價格上漲即刻叛離的人跟品質下降選擇叛離的人,有沒有可能不是同一批人?」這個提問,馬上讓分析變得繁複有趣,在《叛離》第四章有非常精彩的論述。
再從個人捍衛生活品質的差異,赫緒曼的分析概念,也可用來探究社會流動的問題:「機會平等與向上社會流動的結合,真能確保社會正義嗎?」如果上層與下層階級分歧擴大並且變得僵化,上層如何持續往上流動,下層如何緩緩停滯不動,一般並不容易察覺。另外,以為競爭可以一定程度限制獨占也太理想化,有些情況是透過競爭反而幫獨占排除比較棘手的顧客,讓獨占更舒適,從而更強化獨占。赫緒曼用「獨占型暴政」(monopoly-tyranny)來形容這種不太被注意的獨占形態,它的特質是:「無能者欺壓弱小,懶惰鬼剝削窮人,這樣的事更持久而且更令人窒息,因為它既沒有野心,也可以逃之夭夭。」這種不需負責、不被究責的「獨占型暴政」常發生在國營或國家資助的產業,因為盈虧多由大眾買單,即使競爭也無法改善獨占的局面。
赫緒曼把供給、需求、消費者剩餘、公共財、耐久財、產品品質彈性、獨占、寡占、雙占等屬於經濟學的理論概念,巧妙運用於解析政治行動。不過,這本書相對花比較多篇幅在經濟觀點,以有限篇幅處理政治學家所關注的研究對象——國家。赫緒曼在稍後出版的論文,曾特別把「國家」帶進來,探討人們出走(叛離/移民),對移出和移入國的影響2。 可以看到的是,歐洲國家大規模的移民(例如移向北美新大陸),一方面減少歐洲國家內部的社會抗議,另一方面移民在移入的新社會沒有網絡,在當地也比較低調 ;結果呈現,大量移民對移出和移入國的短期影響是減少抗議。另外,可能從人民的出走進一步理解當代民主化的情況嗎?例如,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工人在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初期大規模向法國和德國移入,有促使這些國家更願意通過談判,形成較為民主的程序來留住人民外移嗎?赫緒曼認為這種關係的連結不容易確證,因此獲得的關注不多。不過,異議者離開本國,短期內對威權政權的鞏固顯而易見,這是威權政體處心積慮把異議者驅逐或禁止政敵回國的主因。檢視愛爾蘭人於五〇年代大量出走英國的案例,因為沒有語言隔閡,移出比例非常大,被認為對愛爾蘭國家的存在造成威脅。後來愛爾蘭在一九五八年通過國家經濟計畫,試圖藉由改善經濟政策與條件,防止人民移出與人才流失。赫緒曼提到小國在這方面應變的彈性,跟大國相比,有一定優勢3。
《叛離》出版於一九七〇年,但在一九六八年就以單篇論文發表於史丹佛大學行為科學中心。不妨留意,一九六八年正是六〇年代反叛抗議的高峰。不過,叛離、抗議與忠誠的概念本有古典餘韻,赫緒曼進入老派議題,把它們放在消費社會和公民抗議的現況裡,精妙地鍛鑄這些概念。
這書一出版,馬上造成轟動,廣泛被各領域的人閱讀、討論與運用。然而,赫緒曼並沒有提出一套艱澀理論來刻劃現實,而是派遣日常語彙來捕捉行為動力,藉以展現人們的活動其實是在一個流動的、混合的、不完美的現實中運作。世界雖然充斥著「叛離者」,但並不受「純粹競爭」所支配,人們也不能以毫無拘束的「抗議」來維護自己。在選項上,赫緒曼既不鍾情叛離市場,也不偏好政治抗議;一切都是計算, 可能有「最佳」組合,但組合的情況並不穩定。
這裡,我們值得花一點篇幅來談一下《叛離、抗議與忠誠》被寫出來的前情往事。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阿德爾曼(Jeremy Adelman)撰寫的赫緒曼傳記於二〇一三年出版,書名取為《入世的哲學家》(Worldly Philosopher),不過,這裡的「worldly」一語雙關,表示赫緒曼在社會科學界的「世界性」與「入世」。一般對赫緒曼的介紹,常從他是哥大和哈佛等名校教授,及在一九七四年進入高等研究院,直到學術生命最後,一直在高等研究院的崇高地位。事實上,他在進入學院之前堪稱坎坷的經歷,更值得了解。
赫緒曼自一九三八年在義大利完成經濟學博士學位,一九四一年元月從歐洲逃離納粹踏上美國領土,到一九五八年寫出《經濟發展策略》,其間二十年,都不算有固定工作,寫完《策略》後,甚至還曾短暫失業,這時他已經四十三歲,還在經濟學門。
難道是初始長期不在學院的二十年,讓赫緒曼相對不局限於學院思考嗎?
這二十年裡,赫緒曼被捲進時代的前線。剛到美國因得到柏克萊大學獎學金,不到兩年就寫出《國家權力與外貿結構》(1945)。赫緒曼在書中討論貿易配額、匯率控制、資本投資、經濟戰等議題,以及如何評估世界貿易體系的潛在趨勢。按照當時社會科學的條件來說,有點不尋常:主要是大蕭條時代的經濟學家,多半集中在凱恩斯總體經濟學的討論或多邊貿易和金融體系失靈的問題,很少關注經濟政策和政治體制之間的關聯。赫緒曼在書裡也設計一個統計指標來衡量外貿集中度4,以及外貿如何做為國家權力的工具對或大或小的貿易夥伴產生政治影響。與此同時,德國和中歐轉向威權主義國家,常被看作是因民族特徵而產生的問題。赫緒曼認為,這不僅是經驗差距的誤解,也是概念的失敗。觀察國家主權與世界貿易的交鋒,赫緒曼試圖說明:強國如何以弱國為代價,操縱外貿來增強國家權力。
這個輕嘗學術的經驗,因美國加入二戰馬上被腰斬,赫緒曼本人也投入戰場,在大戰末期甚至擔任聯軍在義大利對納粹軍官審判的翻譯官。從歐洲戰場回到美國,本來想加入財政部工作,最後只在聯儲會擔任政策研究專員,期間調任支援馬歇爾計畫。這之前,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根據赫緒曼三〇年代末期在歐陸的經驗,誤判他與共產黨關係匪淺,讓他每次跟財政部申請工作,都被打回票5。沒辦法在美國找到工作的赫緒曼,在一九五二年前往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觀察經濟發展計畫,起先為世界銀行工作,兩年計畫到期,赫緒曼開起投資顧問公司,在波哥大成為政府經濟計畫和私人投資的顧問。這個走上哥倫比亞的一小步,開啟他做為發展經濟學專家的歷程,也成為美國學界在六〇年代少數的拉丁美洲專家,更因他建立的拉美學界網絡,兩地多國在討論和研究上密切交流,為美國的拉美研究奠立很可觀的基礎。
處處充滿洞察的《國家權力》在出版後,沒有引起太多注意,主要是這本書試圖解答的問題,似乎已是過去世界的事。對照來看,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策略》則寫來介入一個新出現的問題,《策略》被視為是發展經濟學領域最有啟發的一本著作。這本書的重要性,在於提出經濟發展可採取「不均衡成長」的策略;而這個「異議」又創新的概念,來自赫緒曼親自的田野體驗。觀察低度發展國家的情況,赫緒曼以為,應該慎選一兩個戰略部門或行業,給予巨額投資來促進發展,一旦一兩個部門發展起來,就可能帶動其他部門的發展。換句話說,這類國家最可行的發展策略是通過有計劃的不均衡成長來打破低水平的均衡。
縱觀二十世紀五○年代,「均衡成長」才是發展經濟學的共識。不過,許多需要發展的貧窮國家常常面臨勞動力過剩和資本短缺,這樣的組合將造成低水平的「均衡陷阱」——就是低投資、太多窮人、沒有足夠儲蓄,更不用說,先天不良的基礎設施,還有頑固的傳統。均衡發展理論家認為窮國面臨的困境是:阻力和障礙從一部分傳到另一部分,一個角落的阻塞就能阻礙其他地方的進展;因此,需要「均衡成長」來打擊所有障礙或降低障礙。「均衡成長」的劇本也是寫給特定演員演出的,包括具有影響力的外國顧問、「經濟傳教士」和發展專家,他們運用分析工具,調整出微妙的平衡與干預的時間,把不斷演變的系統摩擦最小化。正如赫緒曼常提到,盛裝在宏偉理論的知識外衣,結果可能造成對主要問題的掩蓋。
在《策略》之後,赫緒曼還寫了《邁向進步旅程》(1963)和《發展規劃考察》(1967),被稱為赫緒曼「研究發展經濟學的三部曲」,後兩本著作,一本關注拉美國家經濟發展計畫在政策訂定的政治過程,另一本走進各國城市和鄉野,觀察在地草根在經濟發展如何團結前進。所以,就撰寫手法的親近性來說,與《叛離》最相似的是《策略》,因為兩本書都以很漂亮的手法演繹概念。但要強調的是,赫緒曼的概念從來不是憑空而來。赫緒曼說過,馬克思《資本論》書名的後面應該還有一個副標,題為「一個英國個案研究」,因為馬克思的寫作是立基於對英國工業化的觀察6。 同樣地,《經濟發展策略》的副標就是「一個哥倫比亞個案研究」。
從《策略》到《叛離》,時間相隔十二年,一旦《叛離》成作,赫緒曼就不再隸屬發展經濟學範疇7,而更往政治經濟學和政治思想位移。在本書裡,赫緒曼陳述經濟學家如何霸氣宣稱分析稀缺現象與資源配置所發展的概念,可用以解釋包含權力、民主與國族主義等政治現象。反之,政治學的概念比較少對經濟學提供分析貢獻,這個不對等性,一方面讓經濟學家占領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一方面讓政治學家面對分析工具豐富的經濟學家有自卑情結。不過,赫緒曼也清楚,這種人比人氣死人的情境,也發生在經濟學家面對物理學家的心虛。重點不是各自以強項示人,而是跨到他人領域吸取新知,進而做出貢獻。
當赫緒曼在七十歲退休,時間是一九八五年。還要再等六年,才出版《反動的修辭》(1991)。退休讓赫緒曼在高等研究院有權利而沒有義務,空出時間,有更多自由,他保留著辦公室,可以申請田野旅行補助和研究基金。在退休期間,他一直主張應該在研究院成立政治經濟學講座,聘請跟下列各領域有興趣對話的經濟學者為主,包括社會發展議題、各種資本主義、其他社會科學、倫理學和哲學等。他的期望讓聽到的人覺得任務艱鉅。如果不是赫緒曼以身實踐,如此跨學門的樣態可能不被切實理解。赫緒曼的傳記作者阿德爾曼認為,赫緒曼屬於一個不可回返的智性時刻(intellectual moment),未來恐怕不會再有更多赫緒曼了8。 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從赫緒曼的書,尤其這本經典著作,享受他展現出來的知識魅力9 。本書最後一章最後一段,赫緒曼期待那些被社會或組織成員忽視的反應模式,像叛離、抗議或兩者的組合,可以得到發揮。我們從他語意深長的口吻,巧然發現,透過著作對讀者帶來行動的影響,原來是他心之所繫的夢想。
- 見Jeremy Adelman, 2013. 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頁 371。 ↩
- 見赫緒曼,1981. “Exit, Voice, and the State,” 收入Essays in Trespassing 一書,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頁 246-265。 ↩
- 赫緒曼引用美國社會學家瑞妮.福克斯(Renée Fox)在比利時社會多年研究的心得,作為想像的啟發。福克斯最初選擇比利時作研究場域,就因比利時是「一個小國……比一個大國更容易從社會學的角度理解。」進行研究多年後,她發現與自己原初的想法完全不符:「如果我現在被要求提出涉及國家規模與社會制度複雜性關係的社會學假說,我會嘗試建議兩者之間存在反向關係;就是國家越小,社會制度反而越複雜!」前揭書,頁265。 ↩
- 赫緒曼為測量貿易集中度,曾建構一個集中度指標,這個指標在1950年被一位美國經濟學家赫芬達爾(Orris C. Herfindahl)拿來測量產業集中度,兩個指標的差異只在赫緒曼的指數有開根號,而後者沒有。有一段期間,這個指數一直被稱為赫芬達爾指數(Herfindahl Index)。到了1964年,赫緒曼在《美國經濟評論》一篇短文提及指數的身世,後來被正名為「赫芬達爾一赫緒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見赫緒曼,1964. “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4: 761-762。 ↩
- 雖然從二戰回到美國,自1945-1952年,赫緒曼主要在政府部門工作,從聯儲會到支援馬歇爾計劃,但都屬任務計畫,不是常設職務;如果主管換人,他就必須跟著走人。赫緒曼總計168頁的FBI檔案,是他無法在美國政府找到工作的原因。檔案直到2006年才解禁,之前赫緒曼無從知悉已在「黑名單」,幾次試圖申請財政部工作,都因無法通過忠誠審核,而沒有下落。這個例子,正符合赫緒曼所謂「隱藏之手」的概念,因為不知道已被限制,才鍥而不捨再接再厲嘗試。 ↩
- 見Jeremy Adelman, 2013. Worldly Philosopher, 頁 337。 ↩
- 強調要在一個政治體系背景下理解經濟,總體經濟決策不可能與政權切割,不管這個政權屬於右翼獨裁、社會主義政府、還是多元自由主義政體。作為在直觀審視和歸納分析方面,有敏銳洞察的學者,赫緒曼從未讓自己的經濟學思考,遠離基本的政治關懷,尤其他很清楚,許多經濟分析根本很少注意到意識形態如何導引著政策的決定。 ↩
- 見Jeremy Adelman, 2013. Worldly Philosopher, 頁601。在閱讀上,赫緒曼的涉略廣泛,從黑格爾哲學、馬克思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文獻,旁及法國、俄國、英美文學,在學術的經驗研究領域,則以拉丁美洲國家為專注場域。撰寫論文和書籍都用英文,這是他的第三語言,母語是德文與太太在家交談用法文,博士論文寫作用義大利文,進入田野研究講西班牙語及有限的葡萄牙語。 ↩
- 關於赫緒曼的人格與學術養成,請看赫緒曼著,吳介民翻譯的《反動的修辭》書中兩篇推薦序:吳乃德生動凝練撰寫的<赫緒曼其人其書>(頁9-19);廖美多角度討論的<赫緒曼的學術關懷>(頁21-44),2013,台北:左岸出版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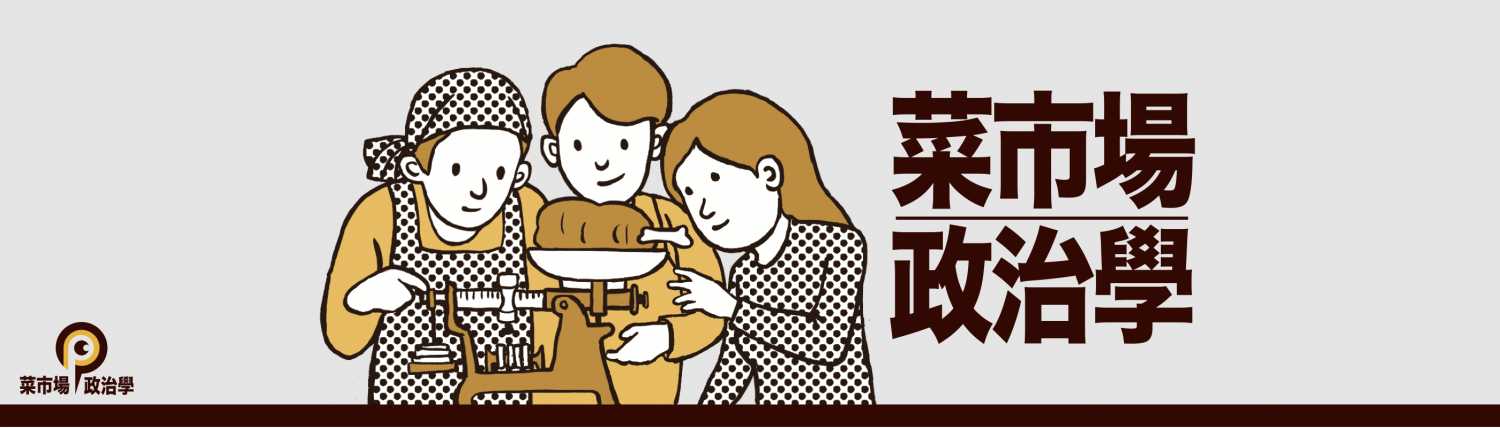

FB帳號:李星逸
抽書
Great
赫緒曼和《反動的修辭》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64/article/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