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家博/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神學與宗教研究系哲學博士
近日泰國曼谷爆發的大規模示威首次提出「改革君主立憲制」的訴求,直接挑戰泰國社會之禁忌。其中的原因,故然包括世代之爭、城鄉差距、極端貧富懸殊、貪腐與武人專政等,但媒體的焦點卻落在泰皇拉瑪十世的德行之上。由於泰皇擁有二十多個妃嬪,生活奢華,登基後長期旅居德國,因而引來國內民眾非議。事實上,民間及政界一直有聲音支持民望高企的漢學家詩琳通公主(Princess Sirindhorn)為攝政甚至登基為女王,而曾為演員的烏叻汶公主(Ubonrat Ratchakanya)甚至在2019年泰國大選接受泰衛國黨(Thai Raksaa Chart Party)提名為首相候選人,公然問鼎權力,引起拉瑪十世不到一日內立即在德國發表聲明認為王室成員不得參政以制止。由此可見,起碼泰國社會內有聲音認為:只要能夠換一個「有德」的國君就好了。
圖片來源:udn 轉角國際
但從政治哲學角度來看,君王的個人道德真的如此重要嗎?若然一個無德的「昏君」後宮三千,天天酒池肉林,但國家歌舞昇平,人民豐衣足食,政通人和,那人又豈能斥之為昏君呢?個人道德與私生活如何,根本與國家的政局及社會經濟發展毫不相干。神宗廿年不上朝,大明朝廷亦依然如常運作。所以,從馬基維利開始,西方政治哲學就開始嚴格區分道德與政治,認為統治者——君主、總統、總理、官員、議員等——之個人道德根本與統治國家毫不相干。這種主張顛覆了大多數人對「政治」的理解與政治家的道德要求。不過時至今日,由傳媒以及大眾對泰皇、美國總統候選人等政要人物私生活的關注來看,顯然大眾不接受「政治與道德分家」的哲學主張。既然如此,到底君主的個人道德對維護國家利益重要嗎?
「德治」思想
重視君王之道德,視政治為道德之事,乃古今中西常見之主張。在西方經院哲學傳統,聖亞奎那於《神學大全》視「政治性達德」為四類德性之一。(《神學大全》II 61.5)如果君王個人違反了上帝的道德規範,國家政治即敗壞,最終會受到上帝審判,此正是《舊約聖經》之主調。
在東方,先秦儒家與墨家正是德治的代表流派。儒家主仁政,墨家主兼愛,皆是由君王個人開始,然後擴展至天下百姓。例如墨子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墨子.節用中》)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言則國家政治清明在乎國君能否實踐兼愛或仁義之德性,以德服眾。
儒墨之德治實有一前設,就是私德與公德相通。只要君主愛人民,就會對人民好,於是就政通人和了。但我們馬上就能問:君主如何能實踐「愛民」呢?相較於墨子提出節用、非樂這些對王公貴族的苛刻要求,孟子提出的「親親」原則就人性化得多。「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只要君主首先家庭和睦,父母、兄弟、姊妹相親(王陽明稱之為仁的「發端處」),就能將此「仁」透過禮制逐漸推廣至與王室疏遠的平民百姓之上,即朱子所言的「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所以周朝禮樂制度的本質就是讓每一個人實踐道德;《禮記.禮運》云:「故禮也者,義之實也」,「仁者,義之本也」,即為此義。
在儒家文化影響下,東亞社會自然份外關注政治人物之私生活與道德。如果一政要出軌,對其妻或其夫不忠,從儒家的角度來看,這人竟然連自己的枕邊人都不愛了,如何能愛百姓呢?怎能治天下呢?這種說法聽起來好似很合理,卻遭到福澤諭吉的批判。
福澤諭吉:私德與公德互不相關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私德與公德相通」之前提在十九世紀即受到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的批評。在《文明論概略》裡,福澤就私德與公德進行區分:「凡屬於內心活動的。如篤實、純潔、謙遜、嚴肅等叫作私德⋯⋯與外界接觸而表現於社交行為的,如廉恥、公平、正直、勇敢等叫作公德。」福澤批評孟子「推已及人」之觀念意圖將私德擴展至公德,即無視私德與公德之區分。福澤以法國路易十四年間的宰相李希留樞機主教為例,他身為神職人員,卻為了政治鬥爭而殺人無數,但在他治下法國國力日益強盛。為何李希留有「公德」呢?並不是因為他能將其私德擴而充之,而是他的鐵腕統治為法蘭西王國帶來「效益」。要達到「公德」,就要有「公智」,知道甚麼手段才能為國家帶來最大利益。
那麼私德對統治來說是否一無是處?又不是。福澤認為,私德在「未開化」。
社會有維持穩定的正面作用,只是在文明社會已經毫無政治價值。「在民智未開,剛擺脫禽獸世界的時代,因急於要制止粗野殘暴的舉動,緩和人心,使人類過安定生活,所以無暇顧及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然而,文明逐漸進步,人與人的關係也複雜起來,就沒有理由只用私德一種手段,來支配人類世界了。 」雖然儒學重視人倫關係,但對福澤來說,儒學之「五倫」以私德為本,只能處理君臣父子等關係,仍過於簡陋,無法處理企業、國家之間的關係,而這些關係只講利益,不講甚麼私德。
依賴君王「德治」是社會落後的表現。「仁君賢相關懷人民、忠臣義士舍身以報君王,萬民齊受君王之德化,上下各得其所,都是以人情為主,以德導致了太平,根本不依靠法制。」隨著社會開化,人際關係漸趨複雜,就只好利用無情的法制(「指以防止人作惡為目的的法制」)規範生活,保障大家的利益。
所以,對於福澤來說,君主的個人道德在文明社會裡毫不重要。「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設的。 政府的體制只要對國家的文明有利,君主也好,共和也好,不應拘泥名義如何,而應求其實際。」
黑格爾:內在道德與外在法律之界線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不過,福澤諭吉的重法輕德思想自然會產生一問題:為何君王要為了維護社會的最大利益守法、行公德呢?福澤大概會認為,只要人人奉公守法,社會利益就最大化。但個人何來誘因守法?為何君王等政要要關心社會福祉?人關心「社會利益最大化」,豈不已經是一個道德判斷嗎?這道德判斷到底是私德還是公德?福澤當然可以假設這道德判斷是純然的「公德心」,與私德之「不忍人之心」、「親親」無關,但他卻沒有交代他提出了如此的假設。既然君王不必關心社會福祉,因此他「強政勵治」的唯一誘因就是畏法:他怕違反了法度,會因而被推翻。
但黑格爾則不認同「道德與法律毫不相干」的極端主張。一方面,黑格爾認同道德與法律有必要作出區分,但另一方面,外在法律之存在正好保障了人的個人道德自由,而這個人道德自由最終亦要提昇為「倫理生活」(Sittlichkeit),使個人自覺其於作為國家「公民」之責任。
黑格爾在《世界史哲學演講錄》對道德與法律作出如此區分:法律責任關注與他人相處的「外在環境」,但道德卻是屬於「內在領域」,乃根據「我的自我判斷」決定。故此,從黑格爾的立場來看,區分法律與道德,反而是為了保護個人道德判斷的個人自由。黑格爾點名批評中國儒學與中華法系未能區別兩者,竟然用法律去強迫每一個人實踐道德(例如不孝要斬首),結果就是內外不分,道德行為再不是自律而自主,而是他律的:忠信孝悌只是出於畏懼刑罰,而不是出自真心。
既然法律與道德之區分旨在保障個人道德,則二者並非全然無關。在《法哲學原理》裡,黑格爾引入倫理生活(Sittlichkeit)之概念,認為當個人藉著主觀的道德意志認識到「善」其實有客觀標準,兩者就得到統一。「善和主觀意志的這一具體同一以及兩者的真理就是倫理。」(《法哲學》141)道德指涉個人,倫理則指涉社會整體:人與人之間應當如何生活。但法律只是實現倫理生活之其中一個手段,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生活並非只有政治與法律活動,因為家庭、學校、教會等人際網絡都是倫理的一部分。
黑格爾論君王之「統合」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讓我們回到「君王個人道德」是否重要的問題。無論是平民還是君王,都有責任將其主觀道德提升成「倫理」,方能與他人共同生活。可是,黑格爾認為在倫理生活裡,君王在國家有特殊的地位和責任。
黑格爾是個君主立憲主義者。他將政治國家分成三個實體:
- 立法權:「即規定和確立普遍物的權力。」
- 行政權:「即使各個特殊領域和個別事件從屬於普遍物的權力。」
- 王權:「即作為意志最後決斷的主觀性的權力,它把被區分出來的各種權力集中於統一的個人,因而它就是整體即君主立憲制的頂峰和起點。」(《法哲學》172)
黑格爾認為政治作為倫理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一個從「多」到「一」的統合過程:尋求共識。立法制定了普遍原則的法律,然後行政(執法)將其執行於特定事例或個案中,例如檢察院根據《刑法典》提告殺人疑兇,內閣根據《憲法》組成等等。但國家主權只有一個;「作為民族精神的國家構成貫串於國內一切關係的法律,同時也構成國內民眾的風尚和意識」,(《法哲學》274)因此國家需要有一實體能夠代表這種「民族精神」去統一行政權與立法權,使人知道他們代表相同的「民族精神」,而這實體就是「王權」。
王權包括三個環節:「國家制度和法律的普遍性」、「作為特殊對普遍的關係的諮議」,以及「作為自我規定的最後決斷的環節」。黑格爾同時反對君主專制及民主共和制;民主共和制似乎沒有一實體可以代表民族精神和主權,而君主專制或獨裁者自己只是隨心所欲,無視普遍性以及特殊性之關係,根本不能代表精神進行判斷。君主必須對本國的憲法和文化精神,以及民情、政治、經濟、社會等有充分理解,才能作出「自我規定的最後決斷」。
於是我們就不難發現:當代的君主立憲主義者或多或少都支持黑格爾主義。他們主張君主是其國家之精神領袖,象徵傳統文化的承傳,代表國家主權,但同時君主卻無獨立的行政和立法權。這樣一來,主權超然於行政權和立法權之上。這是總統制國家難以做到的,因為總統同時是國家元首及政府首腦,即主權與行政權不分。
問題在於:君主應如何作出「自我規定的最後決斷」?難道君主必須是個法律哲學家或憲法專家,充當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判案嗎?這恐怕是誤解了黑格爾「倫理生活」之概念,因為法律只是國家精神在倫理生活的其中一個面向,但君主卻要代表整個國家精神。因此,君主還要具有相當的文化判斷力:判斷甚麼才能代表該國之文化。
例如,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大體也確立「和魂洋才」的文化路線。故此,無論是主張脫亞入歐的反傳統主義者,或是主張是古非今的傳統主義者,都不適合登基為天皇,因他未能貫徹「和魂洋才」的精神。所以除了登基大典等隆重禮儀,天皇甚少於公開場合穿和服。當然,天皇可以要求改變日本精神的發展方向,但他必須首先得到百姓的支持,這需要漫長的「特殊對普遍的關係的諮議」過程。
回到「君主的個人道德是否重要」之問題。黑格爾會認為,這是問錯問題了;問題應為:「君主的倫理生活應當如何?」這卻沒有標準的答案,視乎國家文化而變。古代華夏社會以至今日伊斯蘭國家皆為三妻四妾,其帝皇因而後宮妃嬪眾多,並沒有違反其文化之倫理。因此沙特和汶萊臣民不會因為國王妃嬪成群而示威。但如果泰國社會已接受一夫一妻,反對一夫多妻,而泰皇卻後宮三千,就是違反其文化之倫理了。這不是君主「私德」的問題,而是君主的言行與該文化倫理不相稱。當然,君主可以帶領文化改革,要求大家接受新事物;例如身為英格蘭聖公會元首的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支持婚姻平權,正是參與著一場英國重大的文化變革:從歧視走向平權,同時亦代表著聖公會自由派對保守派的勝利。
故此,君主必須作出文化哲學的判斷,得悉自己應遵從哪一種倫理生活,以領導其文化發展。他可以是個改革先驅(如明治維新、拉瑪五世改革),也可以是個保守權威(如慈禧太后、朝鮮高宗),甚至可以只是個傀儡,但他的倫理生活必須合乎一套文化倫理。改革者或保守者為王,皆如履薄冰,因其旨在改變或保留文化精神,而其立場若不得到社會諒解,或會被視之為「不合倫理」;為了使其言行有正當性,君主就要致力樹立權威、建立親民形象。在儒國就做仁君,在佛國就做法王,在基督國度就做基督徒。反而無所作為的傀儡就較輕鬆,除非國家人民非常撕裂(猶如今日的泰北與泰南,馬來西亞的種族等),否則只要做個順從民意的「好好先生」就行了。至於如何選擇,還看各國君主的智慧判斷。
參考書目
亞奎那著,周克勤、高旭東等譯,《神學大全》,第五冊(台南:中華道明會/碧岳學社出版,2008年)
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
黑格爾著,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台北:五南出版,2020年)
作者簡介
譚家博,筆名安德烈,香港作家、哲學家,《九龍叢報》總編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文學士(2013)、英國杜倫大學哲學系文學碩士(2014)、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神與與宗教研究系哲學博士(2020),研究專長為文化哲學、文化神學、齊克果、黑格爾、新儒家、京都學派、東亞哲學、歐陸哲學。著有《香港文化論》,目前為Penana(https://www.penana.com/user/81346/安德烈老師 )及飛天奶茶駐板作家。
Facebook 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asterandrewt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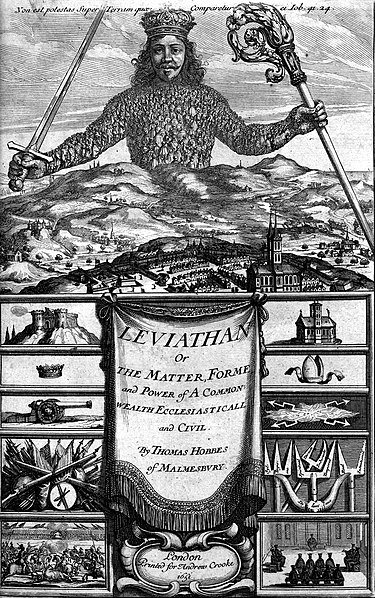
專訪泰國學運領袖:無懼15年刑罰,為何他們激進喊出「王室改革」?https://www.twreporter.org/a/thailand-student-protest-1?gclid=Cj0KCQiAqdP9BRDVARIsAGSZ8AmpDALgS0HWs9IctkRW2KNu-YZKTSoqPbz89FnVlZw5iIvXpk6zgHgaAhfVEALw_wcB
「福澤諭吉:私德與公德互不相關」一段中,「那麼私德對統治來說是否一無是處?又不是。福澤認為,私德在『未開化』」后面是不是多了一个「。」,我感觉「福澤認為,私德在「未開化」社會有維持穩定的正面作用,只是在文明社會已經毫無政治價值。」才比较通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