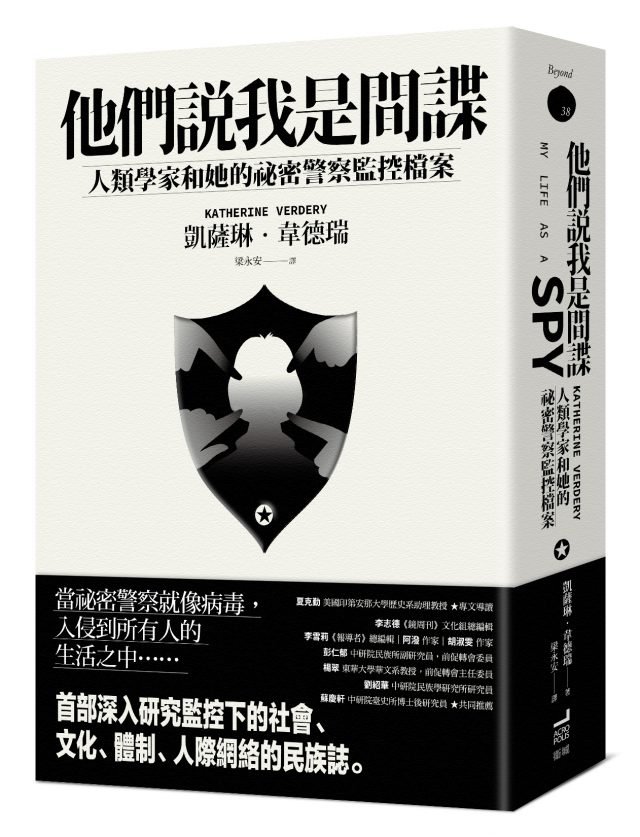◎蘇慶軒/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1
書名:《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
作者:凱薩琳.韋德瑞 (Katherine Verdery)
譯者:梁永安
出版日期:2022/06/01
出版社:衛城出版
連結:博客來
人們回顧過往,通常可以說明自己為何是現在的模樣。對於人生可以掌握的部份,自己的選擇大概影響了日後人生的發展,而另些無法掌握的部份,則可歸於不可知的命與運。不過,受過威權統治的人們卻可能有不一樣的體驗。例如受到國民黨政府壓迫的政治受難者,經過多年關押而出獄後仍須面對政府的監控,不只求職謀生處處碰壁,還要面對社會歧視與孤立,職涯受挫的憤怒與遺憾,讓柯旗化感嘆為「台灣監獄島」。2另一些未受直接迫害但懷疑自己受到監控的人們,在回顧人生時可能不免多了些憂慮,擔心自己現有的模樣,無法歸因於自己的選擇,也不是命與運使然,而是那隱約感受到的政治力量所操弄的結果,甚至猶疑自己是不是誤將政治操弄的影響,當成人生境遇的偶然或必然。
如何理解威權統治的影響與遺緒,成為新興民主社會無法迴避的問題。蘇聯解體後,已有許多研究在重建與探索威權統治下的生活樣貌,突現權力與制度如何左右被統治者的人生,祕密警察滲透社會以鞏固政權的歷史,更加吸引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目光。中東歐社會探索自身歷史的經驗,也有些作品透過各種書寫與翻譯而引入台灣,但相較於主流關注政治、法律與歷史面向上的討論,衛城出版的《他們說我是間諜》則藉著人類學田野研究的特殊性,進一步呈現更加微觀的「威權統治下的人生」。
本書的作者、美國人類學家韋德瑞在冷戰時期多次深入羅馬尼亞進行田野研究,一方面成為共產主義社會研究的翹楚,另一方面也成為羅馬尼亞祕密警察監控的對象,嚴密的監控活動由此產出大量的檔案紀錄。雖然這些檔案紀錄是在描述與分析韋德瑞的活動與思想,但卻與韋德瑞認識的自己不同,其中的歧異甚至與本人的認知相互競爭,讓她重新檢視自己在羅馬尼亞的人生。因此,她以「沒有什麼比閱讀自己的祕密警察檔案會更讓你納悶自己究竟是誰」為開場,啟動一次重新認識自己的過程。
祕密警察檔案中的韋德瑞有許多版本,也有著各自的化名,但無論是哪個版本,在羅馬尼亞祕密警察眼中皆是意圖刺探情報與威脅國家安全的「間諜」。
圖片來源:原文版 “My Life as a Spy” 的書籍封面
人類學家在田野中發展社會關係與取得信任的技巧,是為了融入當地及蒐集資料,因此韋德瑞投注許多心力,以便贏得在地居民的信任與友誼。從這個角度來看,韋德瑞能夠理解田野調查引來秘密警察的懷疑,在冷戰時期實屬合理。然而,祕密警察檔案的不合理之處,在於描述韋德瑞的觀點。秘密警察拼貼著蒐集來的情報,將韋德瑞描寫成數個與她自己認知不同的人,這些「分身」在研究者的外衣下,隱匿著對羅馬尼亞的敵意,使秘密警察必須不擇手段地蒐證,揭穿她的意圖與威脅。
祕密警察檔案讓韋德瑞更加感到衝擊的,是她無法斷然否認檔案內容中的描述,因為祕密警察並非全然虛構出一個陌生人並強加在她身上,而是將她實際的活動,與祕密警察或線民的臆測雜揉在一起,或者對她的言行進行偏頗的紀錄與解讀,因此這些「分身」確實神似韋德瑞記憶中或者田野筆記記錄的自己。祕密警察的描述,讓韋德瑞產生似我而非我的衝擊,使她在比對檔案內容、田野筆記、記憶,以及重回舊地求證檔案內容的過程中,需要重新理解當時的自己與當地的居民。
檔案也顯示,祕密警察為了蒐證而向韋德瑞佈下細密的網羅,讓她難逃祕密警察的耳目。這個情蒐用的網羅,是用韋德瑞的人際關係編織而成,輔以可供竊聽與偷拍的科技工具作補強。不過,這個網羅不只用於情蒐,也用於滲透與影響韋德瑞的言行思想,包含阻撓她的研究進度、左右她的想法,甚至探弄她的人性弱點,以便誘使她產生有利於羅馬尼亞共產統治的觀點與認知。換言之,監視是為了控制,而監視與控制構成了祕密警察掌握韋德瑞生活的動態過程。
為了建立監控韋德瑞的網羅,祕密警察需要從她身邊招募線民。當年與韋德瑞相遇相識的人,可能在檔案裡也有著不為她所知的「分身」,他們在普通人的外衣下,隱匿著情蒐與側寫韋德瑞生活的任務。這些線民與韋德瑞的交情深淺不一,其中有些人與韋德瑞往來時,曾讓她感到愉快,例如熱情招待她的「雅各布」夫婦,但這些愉快的經驗其實是祕密警察授意經營的,而讓日後閱讀檔案的韋德瑞備感難受。有時祕密警察為了更深入地洞窺韋德瑞的秘密,而利用她年輕時活躍的性生活,一方面壓迫曾與韋德瑞發生親密關係的男性,要他們必須向祕密警察舉報她的動向,另一方面也鼓動其他男性向她求歡,以便刺探更多情報。或者,祕密警察決定介入韋德瑞的研究,試圖將她從依賴與人往來的人類學家,轉變成依賴圖書資料的歷史學者,因此一方面讓她難以推進實地訪查的進度,另一方面在她被迫倚重研讀圖書資料時,派了可以協助詮釋資料且受她信任的「斯特凡」在她身旁,以便達成日後祕密警察坦承的目的:「我們想讓妳愛羅馬尼亞」。
經過比對記憶與田野筆記,韋德瑞從檔案中認出了線民,並探訪其中幾位。由於祕密警察監控用的網羅是用她的人際關係編織而成,因此在探訪線民的過程中,韋德瑞發現身旁曾發生自己從未意識到的人際關係爭奪戰。
韋德瑞作為外來者,需要經營與取得當地居民的信任,才能展開田野研究;與此同時,祕密警察為了在韋德瑞身邊佈線,就需要吸收她所信任的人,才能貼身監控。換言之,越受到韋德瑞親近與信任的人,越可能成為祕密警察威脅利誘的對象,這些人必須在背叛友誼或承受迫害之間作出選擇。韋德瑞當年不知道的是,她所經營的某些人際關係在無意間成為自己的護盾,與祕密警察試圖收緊的監控網羅相抗。不過,這不意味著這些願意守護韋德瑞的友人都能安然無恙,當祕密警察無法侵入與瓦解她的某些人際關係後,有時會強力介入與切斷連結,讓她的友人失業、恐懼或流亡,就像韋德瑞熟識的比爾曼夫妻,最終失去工作與流亡德國。延伸監控的需求,韋德瑞發現祕密警察因她的到來,而得以深入過去不易滲透的鄉村,擴展了國家統治的範圍。
圖片來源:紐約市立大學網站
本書更精采的地方在韋德瑞重新梳理人際關係的過程,無論是她探訪過去熟識與信任的朋友兼線民,或是與經手監控業務的祕密警察面談,都曾歷經一番心境上的轉折,而可窺見人性受過威權統治刻劃後的明與暗。然而,韋德瑞終究是外國人,因此即使她的人生與秘密警察有了交集,也不會盡受威權統治左右,最終仍然可以是自己命運的主人。
就在本書於台灣出版的同時,大量監控檔案在台灣開始出土,這些檔案出自威權統治時期情治機關之手,檔案裡的人被情治人員或線民深淺不一地刻畫出另一種人生。與羅馬尼亞祕密警察相似,維護國民黨政權的情治機關也是從被監控者的身旁招募線民,透過人際關係掌握被監控者的動向,並軟硬兼施地影響他們的認知與選擇。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提出的報告指出,情治機關侵害被監控者的隱私,細密地記錄他們的一舉一動。例如受促轉會委託的林國明教授研究團隊,尋訪到的一位受訪者,在翻閱自己監控檔案後說道:「好像我們就是關在籠子裡面的動物這樣在看」。3 與此同時,協助情治機關建立網羅,以便關住被監控者的線民,大部分來自被監視者的「親朋好友」,因此閱覽檔案讓被監控者的人生出現裂痕,當年的學運領袖、現今的立委范雲便感傷「曾經共同打拼的同志情誼與信任,好像在一夜之間被敲碎」。4 更糟的是,相較於羅馬尼亞民主化後在檔案開放與面對歷史的政策上有所進展,台灣才剛開始受到衝擊。因為情治機關的阻撓而無法辨識檔案中的線民,讓有些被監控者在閱覽檔案後更感挫折,只能在當年志同道合的同伴中猜疑誰才是情治機關的線民。5
人們因為本能,需要互信互賴與發展人際關係,但在威權統治的影響下,人們卻不免猜疑,關係的本質究竟是圓滿人際互動的需求,還是得寸進尺的侵犯與操弄。韋德瑞的觀點是個鮮明的對比,映照出成長於民主與威權時代的差異。出身美國而自小崇尚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價值的她,在重新認識自己與叩問研究羅馬尼亞的人生時,警覺「必須拋棄在美國文化脈絡中一種主要以個人自主角度思考的傾向」,因為在威權統治下,個人不是自己人生的主宰。相較之下,受過威權統治的人們,可能懷疑自己人生的境遇是否曾受威權統治刻劃與左右,而有著「我不是我的我」的複雜情感。若人生的選擇無法擺脫被威權統治操弄的痕跡──即使像是從技術官僚一路「被栽培」至黨國層峰權位的繼承,沒有選擇地在威權統治者的視野裡機巧謀算與兢兢業業──當人生走到盡頭時,恐怕不免懷疑「我是不是我的我」。或許,這不僅是個人曾被長期監控而不免叩問人生的問題,恐怕也是受過威權統治的社會面對過去時待解的疑惑。
面對過去必然艱難,然而唯有「歷經自我,才有自由,國家也是這樣」。6
※注釋
- 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研究員。感謝衛城出版社的邀稿,也感謝作家阿潑對本文初稿的意見,文責由作者自負。 ↩
- 柯旗化,2008,《台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高雄:第一出版社。 ↩
- 林國明,2019,〈威權統治時其校園與社會監控之研究訪談/H17〉,轉引自促轉會,2021,《任務推動及調查結果報告書 第二部 探求歷史真相與責任的開端:壓迫體制及其圖像》,頁2-413。 ↩
- 范雲,2010〈告密者、我和我的被監控檔案(中)〉(范雲 FAN, Yun 臉書粉絲專頁),轉引自促轉會,2021,《任務推動及調查結果報告書 第二部 探求歷史真相與責任的開端:壓迫體制及其圖像》,頁2-414。 ↩
- 如有人指出「我們這十個人裡面都是我當初的好朋友,我亂猜害了其他三個人,他們是不是也變成是受害者,我們其實集體都是這一個監控下的受害者」。促轉會,2021,〈當事人意見調查計畫訪談/G2〉,促轉會第1105100190號簽,轉引自促轉會,2021,《任務推動及調查結果報告書 第二部 探求歷史真相與責任的開端:壓迫體制及其圖像》,頁2-419。 ↩
- 李桐豪,2020,〈【近看李登輝】我不是我的我〉,《鏡周刊》。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200226pol001/,最後瀏覽時間:2022年5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