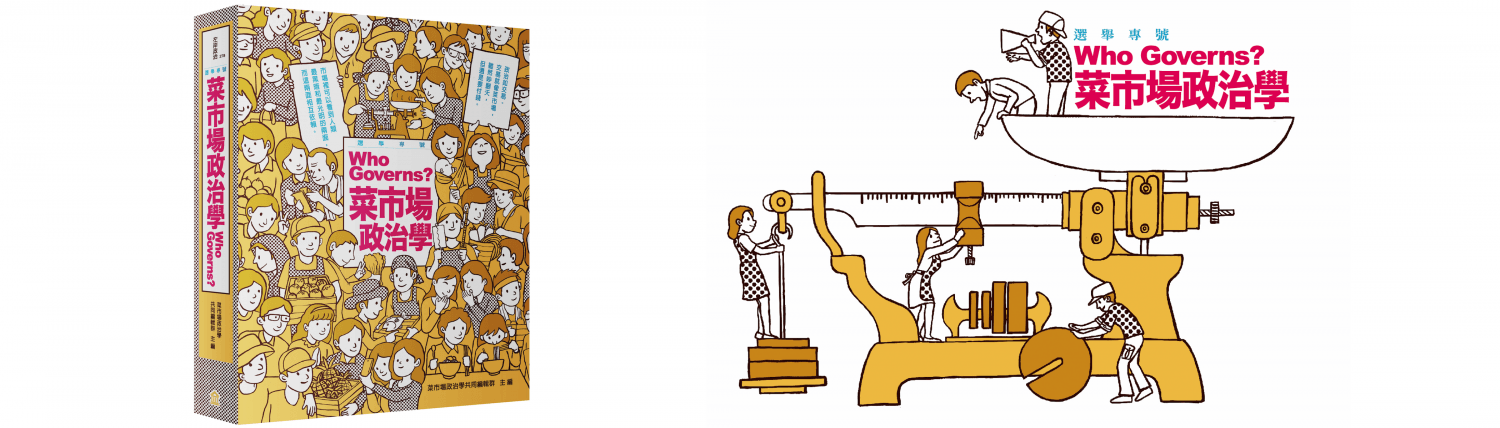◎陳宏銘/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本篇轉載自《東吳政治學報》-溪望政治學的網頁
https://sites.google.com/view/soochowjps/
※《東吳政治學報》延伸閱讀:
第四十卷第三期二十一世紀憲政體制的採行和變遷:區域與全球趨勢之探討
關心台灣憲政體制運作的人,大都對總統制、議會制和半總統制這三種體制耳熟能詳。即使對「議會制」一詞感到陌生,台灣人也多熟悉另一個習慣的講法:「內閣制」;並且就算是不認識「半總統制」,當聽到較接地氣的說法:「雙首長制」時,也會恍然大悟。不必是政法領域專業人士的讀者也多不意外,長久以來內閣制和總統制是全球較居優勢的兩種體制,並且由英國和美國分別扮演領頭羊的角色。不過,世局多變,到了二十世紀末全球第三波民主化進入尾聲,一時間湧現了包括台灣在內的三十多個半總統制國家,這造成憲政體制全球版圖的大變動。傳統上憲政體制的二元競爭,轉換為「總統制、議會制、半總統制」三分天下的新局面。
時序再邁入二十一世紀後,最新情況又是如何?鼎足而立的當代政府體制類型分佈,是否維持不變?
憲政體制的選擇與定位,是一項具有濃厚的規範性價值問題,也一直是台灣憲政發展中持續爭論的重要實務課題。一個國家的憲政體制設計和其對民主政治的影響,是國際政治學界研究的焦點,而且這個議題至今仍然充滿活力。儘管已有大量相關文獻,但對於本世紀最新的全球發展趨勢的系統性觀察,仍顯不足,這限制了我們對實務的理解和理論的發展。作者想要藉此和讀者分享個人最新的觀察。
理論可以讓我們以簡馭繁地面對複雜的現實政治,關於憲政體制的選擇,學者們也提出一些理論觀點。其中,如強調文化與地緣因素、殖民和示範作用、歷史遺緒等等影響,對於總統制和內閣制在各國的採行具有相當的解釋力。美國三權分立憲政體制的示範作用,影響了臨近中南美洲國家總統制的仿傚。英國及其文化主導的地區,則形成了議會民主制。至於二十世紀末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時代因素,則解釋了半總統制被大量國家採行的原因。就像台灣一樣,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的人民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多嚮往能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總統),但又不想讓制度一下子出現太劇烈的變動,因而維持原有內閣政府向議會負責的體制;還有,民主化過程中多少都出現新舊的政治勢力間的競爭,它們之間對制度各有偏好,角力的結果就有些妥協性,也造就了具有混合制特性的半總統制憲政工程。
不過,到了本世紀後,上述理論在解釋最新全球憲政體制的佈局和變遷時,似乎又面臨了限制,而力有未逮。這需要同時進行區域性和全球性兩種層次的觀察,甚至是再藉助個案的歸納,以分析總體發展趨勢。這項研究工程相當浩大,即使能做得到,也不易面面俱到,作者個人只是拋磚引玉。
三種憲政體制的分布數量轉變趨勢
研究發現,本世紀三種憲政體制的區域分佈數量之對比,在穩定中存在變動性。在區域層次上,總統制的優勢仍持續集中在中南美洲,其次是非洲;內閣制則在歐洲(扣除後共產主義地區)、加勒比海地區和大洋洲等地,相對地較為普遍。半總統制的優勢區域,則明顯出現在東歐及巴爾幹後共地區,其次是中亞、北亞和西亞等地。變動跡象特別值得留意,其中,中亞、北亞、西亞和非洲,以及東歐及巴爾幹(後共)等三個地區,是相對上制度轉型個案最多的區域,並且在這些地區中,半總統制國家的數量也相對較高。這顯示半總統制變動機率相對較高,這進一步增加了這些區域制度變遷的案例。相對而言,虛位元首的議會制變動機率最低,因此該區域的制度變遷案例較少。
本世紀全球憲政體制的採行和分佈,雖然可以追溯自長期的區域和文化以及歷史遺緒因素,但對於後續的變遷情況,這些因素較無法提供解釋力。與此同時,民主化浪潮的因素,對本世紀前諸多新興民主國家的憲政選擇經驗具有解釋力,但對二十一世紀初的局勢則不復存在。固然在北非和中東地區出現「阿拉伯之春」的革命風潮,但後來多數國家的憲法秩序無法穩定建立。在此情況下,變動的關鍵因素就在於全球半總統制國家的演化,還有特定國家內部政治運作的中短期變數。尤其是取決於這些國家內部不同政治勢力的消長,以及具有主導力量的政治菁英、黨派的制度偏好與互動,因此結果也充滿不確定性。
進一步的,我們可將制度的「變遷」(或演化),視為制度「選擇」的長期發展過程,並區分三種型態:完全轉型、次類型間的轉型、局部轉型。研究結果揭示,大部分全球憲政體制的完全轉型案例,出現在以半總統制為起始點,再朝議會制或總統制方向轉換;其中轉向總統制的國家(葛摩,2002、肯亞,2010、安哥拉,2010、土耳其,2018、查德,2018、吉爾吉斯,2021),比轉向議會制(亞美尼亞,2018、喬治亞,2018、摩爾多瓦,2001-2016)相對略多一點。且兩種轉型相關案例都出現在新興民主國家或政治轉型國家中,成熟的民主國家,幾乎未見跨類型的完全轉型案例,顯見後者憲政體制遠較前者穩定。
還有,脫離半總統制的數量,略高於轉向半總統制;但總統制、議會制及半總統制三分天下的格局不變,在國家數量上,依序為議會制、半總統制、總統制,再扣除非民主國家後,排序依然如此。再者,沒有任何在總統制和議會制之間進行直接轉換的案例。即使出現如土耳其(2014-2018)在本世紀由議會制轉為總統制的特殊個案,也是中間經歷過短期的半總統制階段。換言之,制度轉型的起始型態或終點型態,幾乎其中的一端是半總統制。這顯示,總統制和議會制之間,是一種難以直接跨越的「大轉型」;半總統制則提供一種變動較小的權宜選擇,以致於是新興民主國家或政治轉型社會最多採用的制度型態。
研究也發現,由半總統制轉向議會制,要比轉向總統制,有較多的個案民主程度相對提升。但由於轉向議會制的個案較少,因此轉型模式與民主表現兩者的相關性,僅能持保守的估計。另外,考慮半總統制存在次類型,譬如在總統議會制(president-parliamentary regime)與總理總統制(premier- presidentialism)間的互相轉換中,分別都有相關個案伴隨民主程度的提升,因此同樣的,想要論斷由某種半總統制次類型改採另一次類型,必然有利或不利於於該國的民主,恐怕還不到時候。
小結
總結而言,有兩個理論上的關鍵因素,對本世紀全球憲政體制發展更具解釋力,一是全球半總統制的演化趨勢變數,二是特定國家內部政情的發展。前者是由於半總統制的相對易變性,構成了憲政類型全球發展的核心變數;後者則與主要政治勢力和菁英的制度偏好、策略互動密切相關,尤其是近來常有民粹型政治人物、或政治強人的崛起,這種政治人物往往對一國的政治運作和制度選擇,有不少的影響力,乃至主導性,這是國家制度選擇和變革的關鍵短期因素。作者希望上述研究發現,能對憲政體制選擇在實務及理論上的探討,帶來新的訊息和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