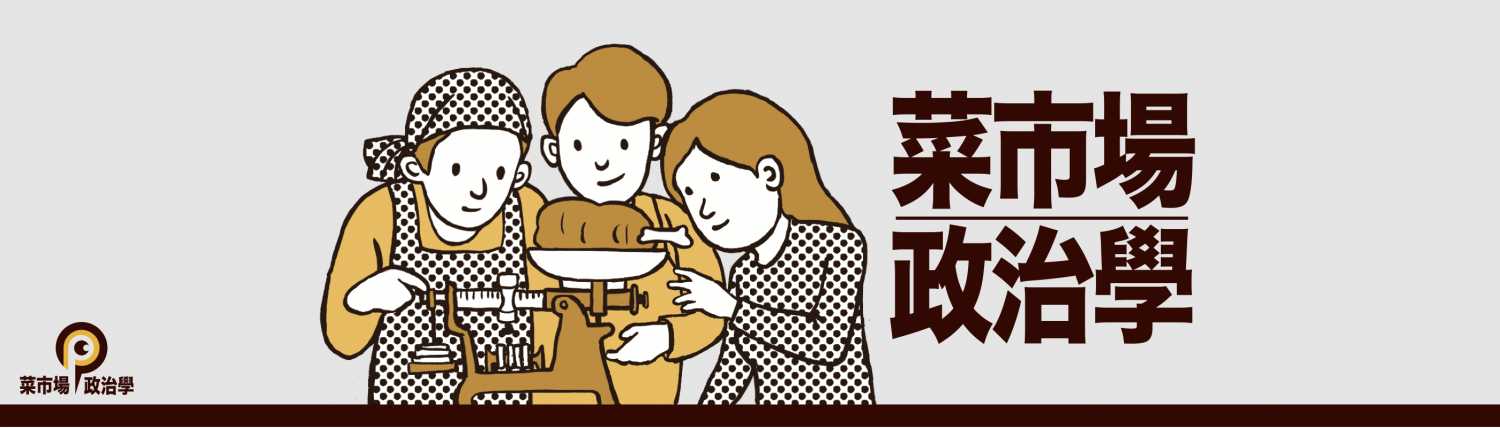◎陳亮宇/荷蘭萊登大學區域研究所博士生
※本文原發表於Oranje Express荷事生非,經荷事生非同意後轉載及編修,原文連結。
【本文上篇連結】
在上篇裡面,我們了解到中間偏右的政黨,在這次選舉獲得較多選民的青睞,而極右勢力並不如預期那樣驚人。接下來,我們將繼續討論荷蘭政黨政治從過去到現在的變化。這次大選,媒體和評論大多以荷蘭多黨林立之現象指出「荷蘭政黨結構走向分裂化」,並舉極右勢力崛起為例主張「荷蘭政治文化正在走向極化」,真的是如此嗎?
二十世紀的三大政黨家族:社會民主、自由派與基督民主
在討論今日荷蘭多黨林立的現象時,不妨先從傳統的三大政黨家族開始說起:(1)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ts),或所謂的左派;(2)自由(liberal),或所謂的右派;(3)宗教(religious),特別是所謂的基督民主(Christian democrats)。一般說來,社會民主家族的左派政黨(例如PvdA和SP)比較強調政府在維護平等與分配正義過程扮演的角色。在社會與經濟問題上,他們傾向利用政策工具的介入,來保障勞工、婦女等特定群體的權益。右派政黨(例如VVD)傾向減少政府對個別公民的干預(照顧),鼓勵個人自行決定其利益,以及支持市場自由化的運作機制。宗教型政黨(主要包含天主教和基督教政黨,例如SGP、CDA和CU)將聖經和教義導入政治思維,認為政治必須守護若干教會認為重要的價值。因而,在某些具爭議的倫理道德議題上,例如墮胎、安樂死、大麻和同性婚姻等,他們有其堅持。此外,保守的SGP甚至主張,男性和女性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唯有男性才擁有投票權,且直到2006年以前,SGP都還設有男性成員才能成為黨員的規定。
綜合三個政黨家族的主張後將可發現,我們不太容易將所有荷蘭政黨放置在一個簡化的意識形態的左右光譜上。其困難處在於,討論社會經濟議題,以及道德倫理議題時,政黨們所處的位置恰好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在社經議題上,社會民主政黨在左、自由派政黨在右,基督民主政黨大約在中間;而在道德議題上,世俗化的社會民主和自由派政黨將相鄰在左側,基督教政黨和基本教義派則在右側(保守)。因而,當我們指涉所謂極端保守的極右派時,可以是經濟政策上的保守,可以是民粹的、排外的,亦可能是恪守教義的等等。

圖片:雖然說不應該把複雜的荷蘭政黨簡化成一個從左至右的光譜,但如果真的想這麼做的話,不妨參照這張由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製作之圖示,而且我傾向把光譜右邊的基督教聯盟(CU)和隔壁的基督教民主黨(CDA)互換位置,因為一般而言,CU較CDA更保守一些。另外,該圖還少了四個政黨:第一為動物黨(PvdD),大約落在綠色左翼(GL)和工黨(PvdA)附近,偏左;第二為五十歲以上黨(50Plus),大約位於D66附近的中間溫和地帶;第三為基督教政黨中的政治改革黨(SGP),大約落在CU和PVV之間,屬於相當保守的一群;最後則為民主論壇(FvD),落在和PVV差不多位置的極右翼。圖片來源:Dutch election results
柱狀結構的社會體系
二十世紀中葉以前,荷蘭政黨在各政策議題上的態度相對明顯,選民可以比較不費力地辨識出與自己立場相近的政黨家族,並在選舉時投給某個政黨。特別是荷蘭在二十世紀初以來形成的柱狀化(verzuiling, pillarization)社會體系,更助長了此種現象。舉例來說,一個天主教家庭成員,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閱聽的報紙和廣播、參加的運動球隊或俱樂部、公會、工會與保險體系,購物的商家,買車修車,通通都是天主教的,其結婚對象與所生子女自然也是天主教徒。當選舉到來時,他們會將票投給天主教人民黨(Katholieke Volkspartij, KVP)。於是,從出生到搖籃,從社會底層至菁英階層,每一個宗教或群體擁有其通往棱柱頂層的階梯和網絡,一個人終其一生,可以不需要與其他「非我族類」互動往來、合作貿易,也不可能與信仰不同者結婚。1在1950年代末,天主教高層甚至還一度限制自身群體成員,和其他群體(特別是社會民主黨派)之間的互動或合作。與此同時,即便同樣信仰基督教的新教徒當中,屬於正統喀爾文(Calvinism)教派的保守群體,以及較為自由、世俗化的教派之間,也是有所區隔而互不跨界的。

圖片:荷蘭柱狀化社會結構的幾根支柱,像是自由派、基督教、天主教、社會主義等等。不同群體的成員,各自有其求學的學校、閱聽的媒體、宗教信仰和投票的政黨。資料來源:wederopbouw, welvaart en polarisering: de jaren ’50 en ’60
不過,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隨著農業和工業社會轉型,荷蘭的中產階級人數逐漸增加,勞工階級則在減少,居住到近郊的人口比率也在上升。當大眾逐漸習慣現代式的個人主義生活型態,原本分屬不同棱柱群體的社會逐漸聚合,跨宗教和群體的往來和婚姻成為可能,政黨意識形態之間的界線正在消褪。隨著宗教世俗化程度增加,不僅導致荷蘭全國許多教堂乏人問津乃至停用,泛基督教政黨的支持結構也在變遷,間接推動了包括天主教政黨KVP在內的政黨重組。
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走向充滿小黨的大平台
影響所及,若干天主教與基督教政黨成功整併,像是荷蘭的基督教民主黨(CDA),便是由天主教政黨KVP、基督教的荷蘭改革教會政黨CHU,以及另一支改革教派政黨ARP在1973年完成整合。2進入1990年代,除了結合共產黨、和平主義者和激進分子組成的綠色左翼(GL),荷蘭政府還在1994至2002年間,出現由左派PvdA、中間溫和D66和右派政黨VVD共組聯合政府的紫色內閣,3雖然這並非歷史上首次「左右共治」,卻是頭一遭沒有任何一個基督教義政黨(特別是CDA)加入執政聯盟的政府。值得注意的是,許多較具爭議的法案,例如安樂死、有限度合法販賣大麻,以及同性戀婚姻等,都是在該時期通過。另一件同樣重要的政策方針為,政府更強調移民在社會與經濟方面的參與,更致力於協助移民融入荷蘭社會,包括在學校學習荷蘭語,以及提升移民在教育、就業,以及居住等等方面的水準。因而,除了宗教因素導致荷蘭柱狀社會結構的鬆動之外,紫色內閣是另一波化解柱狀群體差異的時期。

圖片:1970年代後的荷蘭,柱狀社會結構已經出現鬆動和變化,最明顯的例證是三個基督教和天主教政黨合併成為基督教民主黨(CDA)。資料來源:Twee geloven op één kussen
二十一世紀以來,各種議題導向的新興政黨也逐一浮現並在國會取得席次,例如2002年成立的動物黨(PvdD),以及2009年成立的五十歲以上黨(50Plus)。且這些政黨並不僅關心起家的單一議題,也會將觸角延伸至其他政策主張。舉PvdD來說,除了訴求動物福利以外,他們也針對現行歐盟運作模式提出批判,包括其不民主的組織結構和程序,和過度強調成長及貿易的邏輯。目前,無論是和立場較傳統左派更積極的進步派政黨,或者更往極右靠攏的民粹主義政黨,皆在國會佔有一席之地。4
同時,另一個現象為,隨著當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問題日趨複雜,一個政黨可能在不同議題上,同時混雜著左和右的觀點。最有意思的例子,莫過於一直被貼上極右與民粹標籤的PVV,雖然在其2017至2021年之政黨政見中洋洋灑灑列出多項對付穆斯林的作法、直接民主,以及退出歐盟等民粹式主張,以及「減少藝術、創新、文化與發展援助領域的預算」,但也提到要「將退休年齡降為65歲,並提供年金」,以及「恢復原先刪減之健康照護支出」,後兩者顯然是社會民主黨派才會支持的主張。當有論者認為,PVV的社福政策只是用來吸引選票的競選口號的同時,或許真的有部分來自中間偏左的選民,因不滿上屆工黨配合政府大砍社福的施政,而轉而投向PVV呢。
今日荷蘭,不僅實際加入政黨的黨員人數在下降,選民的政黨認同和結構式投票也已不如過往。當政黨色彩式微時,強調政黨候選人的個人特質,特別是透過強化選票上的頭號候選人(lijsttrekker)形象以吸引選民的作法,變得越來越普遍。像是這回2017年的選舉,除了VVD的呂特和PVV的威爾德斯是媒體焦點以外,綠色左翼(GL)的黨魁克拉佛(Jesse Klaver)也相當受到關注。年紀僅30歲的小帥哥克拉佛,父親是摩洛哥裔,母親則是荷蘭和印尼混血。由於外型與加拿大現任總理特魯杜(Justin Trudeau)相似,時常被媒體拿來宣傳,相信也為政黨吸引到不少迷哥迷妹們的選票。而說到媒體,在這個網路發達的世代,社群媒體與網路傳播已成為重點宣傳工具,幾乎所有政黨和黨魁本人,都會透過諸如facebook和twitter等媒介向外界互動,直接傳達來自候選人的即時消息。

圖片:左為現任荷蘭綠色左翼(GL)領袖Jesse Klaver,右為加拿大現任總理Justin Trudeau,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帥呢?資料來源:Green politician Jesse Klaver is being called the Dutch Justin Trudeau
民粹主義與反穆斯林之極右翼勢力的崛起
討論了傳統三大政黨家族和荷蘭政黨的演變趨勢,不得不再談談近期荷蘭的民粹主義,以及主張反移民和伊斯蘭政黨之極右翼的興起。1960年代前後,欲從二戰後極力復甦的荷蘭,開放引入一批土耳其、摩洛哥等地之外籍勞工,以補足工業和各方面生產所需之勞動人口。1990年代以來,這些移民的第二代與第三代陸續在不同城市地區落地生根,累積可觀的人口數目,再加上伊斯蘭信具仰排他性之故,彷彿正在荷蘭社會形成另一個柱狀結構。5
即便荷蘭社會對這批穆斯林為大宗的移民族群相當感冒,卻也沒有人在政治上公開表達對他們的敵意,而大多強調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包容(tolerance)或融合(integration)等價值。二十一世紀初,荷蘭政治史上的傳奇人物,民粹主義領袖佛陶恩(Pim Fortuyn),首度公開批評當時荷蘭對移民的態度和文化多元主義,表達對於「荷蘭伊斯蘭化」(Islamization of the Netherlands)的擔憂。本身為同性戀者的佛陶恩,也攻擊「恐同」的伊斯蘭不尊重那些荷蘭一向最強調的人權、自由和多元價值。在2001年美國發生了911攻擊事件後,佛陶恩的言論也廣泛受到注意。
2002年的國會大選前,佛陶恩離開原先的宜居荷蘭黨(Leefbaar Nederland),籌組新的佛陶恩黨(List Pim Fortuyn, LPF)參加大選。在憑藉個人魅力和演說技巧吸引選民的同時,媒體也不斷炒作他極右翼的特質。要注意的是,除了伊斯蘭問題以外,佛陶恩之所以能喚起廣大民眾支持,還在於他點出了當時荷蘭政府的運作缺點,像是權力集中在內閣中的一小撮人,若無共識便傾向暫緩某些政策議題,以及在各種妥協後,政黨之間形同沒有差異,也無法代表各群體的人民了,因而,他訴求直接連結人民和政治。根據民調,當時聲勢如日中天的佛陶恩,極有可能在選後成為下一屆總理。然而就在選前9天,他遭到一名左翼人士槍擊後身亡。選後的LPF雖然以國會第二大黨之姿(17%的得票率和26個席次)加入CDA和VVD的執政聯盟,但因群龍無首、成員們也不爭氣,幾個月後便導致執政團隊起了內鬨,導致2003年再次進行國會大選。然而,失去精神領袖的LPF這回只獲得5.7%得票率和8個席次,從此一蹶不振,並於2008年後解散。
不過,荷蘭境內掀起的族群情緒已經無法止歇。令人難過的是,2004年11月,反伊斯蘭的電影導演提奧‧梵谷(Theo van Gogh)遭到一位激進穆斯林暗殺。6這兩起暗殺事件後,促使荷蘭各政黨重新審視過往的移民政策,也傾向更嚴格的限制。當今最為人熟知的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當初便是受到佛陶恩啟發,隨後在2006年創立自由黨(PVV),並將其定位在反伊斯蘭、反歐盟的極右翼政黨。女性政治家,擔任過荷蘭融合與移民部長的費爾東克(Rita Verdonk),7也在2007年發起成立荷蘭驕傲黨(Trots op Nederland, TON)的運動,並一度在民調中獲得高度評價。然而,TON雖然在2010年的地方選舉有些許斬獲(1.24%得票率和61席),卻沒能在全國大選取得席位,稍後也逐漸消失在政壇。如今,荷蘭境內的反穆斯林問題和種族衝突的情緒確實嚴重,威爾德斯和PVV代表的激進勢力在荷蘭社會如何發展下去,以及,傳統的主流大黨(無論左派和右派)如何受到PVV的影響,今後又如何面對棘手的族群問題,則有待繼續觀察了。
多黨林立對於組閣的影響
這次選舉我們還可以發現,傳統大黨的得票率下滑,不再壟斷大局。早先,若將前段班幾大政黨(特別是CDA、VVD、PvdA以及D66)的得票率相加,就可能達到甚至超過全體的八成,這些政黨也常是組閣的固定班底。但自二十一世紀以來,傳統大黨的加總得票率只剩下五六成,多數政黨就算取得了下議院席次,其支持率都不超過20%。如此意味著,當選後最大黨要籌組內閣時,將可能面臨得挑選不只一兩個夥伴,而是三至四個政黨才能形成執政聯盟,且當中可能也包括意識形態與其他結盟政黨相左的情況。因而,組閣過程以及執政政府內部的協商成本增加,連帶也可能影響施政運作的穩定性。此外,若再考量由荷蘭省議會代表投票決定的荷蘭國會上議院(Eerste Kamer)的75個席位,將可以發現,由下議院多數黨組成的聯盟,卻不保證同時掌握上議院的過半席次。是以,雖然下議院第一大黨沒選擇某些政黨組閣,也必須和其保持良好互動關係,以利下議院送出的法案,在上議院獲得支持。

圖片:荷蘭幾大政黨領袖在選前一天(2017年3月14日)於海牙舉行的最後一次辯論的合照。由左至右分別是民主六六黨(D66)的Alexander Pechtold,自由黨(PVV)的Geert Wilders,社會黨(SP)的Emile Roemer,動物黨(PvdD)的Marianne Thieme,綠色左翼(GL)的Jesse Klaver,自民黨(VVD)的Mark Rutte,基督教聯盟(CU)的Gert-Jan Segers,工黨(PvdA)的Lodewijk Asscher,以及基督教民主黨(CDA) 的Sybrand Buma。值得注意的是,僅有動物黨領導人為女性。圖片來源:Dutch PM Rutte claims win over ‘wrong kind of populism’
結語:在現行制度下,不必過於憂心荷蘭政黨會走向極化
最後,回到我在一開頭提的兩問題:許多媒體評論都表示,荷蘭的政黨結構走向分裂化,和荷蘭的政治文化正在走向極化,真的是如此嗎?
坦白說,我的答案可能相對樂觀一點,因而和一般媒體評論有所差異。關於荷蘭政黨分裂化的問題,即便荷蘭參加選舉與成功獲得席次的政黨數量增加了,而傳統大黨的得票率和席次則在下降,但大致而言,新興政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主張,不過是較傳統大黨的立場更鮮明一些、辨識度更高一些而已。就「多元」的觀點來說,那些打著單一議題起家的政黨,恰好補足了過往為傳統大黨忽略的議題領域。此外,這些單一議題政黨進入國會後,也必須發展出對其他廣泛的社會經濟和倫理道德問題的立場,混入既有的意識形態光譜。所以,我寧可說荷蘭的政黨變得更多元了,而不是分裂化了。
至於近期媒體評論最關切的「荷蘭政黨政治走向極化」的問題,如果從政治制度的角度來看,採行比例代表制和多黨制的荷蘭,由於不太可能出現一個獲得絕對多數(得票率超過50%)的大黨,政治菁英之間的權力分享和協商(當然當中也包含了政黨之間的利益交換)才是重點,因為無論任何一個政黨的政策主張,都必須取得若干政黨支持,才可能付諸實現。正是在荷蘭著名的「妥協的政治」下,選前相互對立的政黨,選後依舊可能坐在會議桌上進行談判,討論合作的可能。那些極端激進的政黨(例如本次選舉搶盡媒體風頭的PVV)即便有部分民意基礎,進入國會後,如果無法取得其他政黨的支持,則既不可能執政,也不太可能成功推行法案。除了在表決時投票反對執政聯盟的議案以外,他們也只剩下從社會輿論來影響政策走向了。所以,我傾向認為,正是因為荷蘭的政黨數量多,意識形態和主張多元,激進極端的政黨不太可能將政策導向最極化的路線。

圖片:荷蘭大選的選票。2017年的國會大選,共有28個政黨,1114位候選人名列在選票單上。就性別比例來說,721名為男性,393名女性,女性佔全體的35.3%。不過,只有3個黨是由女性候選人擔任頭號候選人(動物黨(PvdD)、海盜黨(PPNL)和第一條黨(Artikel 1);一半的政黨,也就是14個政黨,將女性候選人列在第2順位。圖片來源:作者攝影。
2017年荷蘭的國會大選,共有28個政黨,1114位候選人名列在選票單上。就性別比例來說,721名為男性,393名女性,女性佔全體的35.3%。不過,只有3個黨是由女性候選人擔任頭號候選人(動物黨(PvdD)、海盜黨(PPNL)和第一條黨(Artikel 1);一半的政黨,也就是14個政黨,將女性候選人列在第2順位。(圖片來源:©陳亮宇攝影)
也許是英國脫歐和美國川普當選總統已經讓眾人驚呆了,當前各國實在承受不起再一個刺激,加上媒體時常渲染和炒作議題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在2016年12月舉行奧地利總統選舉和義大利修憲公投之前,「極右勢力將統治奧地利?」、「歐洲要變天了?」、「下一個未爆彈:義大利?」等聳動的標題攻佔媒體版面,但故事並沒有像媒體說的那樣。這回2017年的荷蘭大選,又是相似的「荷蘭政壇鉅變,民粹抬頭」、「極右勢力將成為荷蘭第一大黨?」「推倒歐盟的第一張骨牌?」、「荷蘭脫歐將成真?」。雖然每一次選舉的激情已是常態,但媒體過於放大某些議題的結果,導致許多內政、教育、環境、性別等等的政策議題,最終沒有受到該有的重視,反倒比較可惜。
※參考資料
Andeweg, Rudy B. and Galen A. Irwin. 2014.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the Netherlands (4th edition).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Besamusca, Emmeline and Jaap Verheul (eds). 2014. Discovering the Dutch: On Culture and Society of the Netherland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Wielenga, Friso and Lynne Richard (translation). 2015. A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Dutch election results since 1918
※延伸閱讀:荷事生非
※推薦閱讀
5張圖看懂荷蘭選舉:本土「特朗普」受挫,民粹主義幽靈繼續縈繞歐洲
- 從前,荷蘭有句俗諺稱作Twee geloven op één kussen, daar slaapt de duivel tussen,英文直譯是Two faiths on one pillow; between them sleeps the devil,中文意思就是「兩個信仰不同的人睡在同一個枕頭上,中間隔著惡魔」,用來指涉當時數量相當稀少的跨宗教婚姻夫妻。 ↩
- 到了2000年,屬於正統喀爾文教派的GPV和RPF,則合併成基督教聯盟(CU)。 ↩
- 最著名的例子,應屬1994年至2002年間,由左派的工黨(PvdA)、中間溫和的民主六六黨(D66)和右派的自民黨(VVD)組成的紫色內閣。其典故在於,工黨象徵之「社會民主」為紅色,自民黨象徵之「自由」為藍色,兩者混合後便是紫色。 ↩
- 其實荷蘭還有各種特色小黨,像是海盜黨(Piratenpartij, PPNL),但因為篇幅關係,就不多介紹了。可參考:荷蘭的巨型選票。 ↩
- 坦白說,伊斯蘭群體也許並非刻意形成的,也可能是融入荷蘭社會過程的非預期結果。例如,當荷蘭家長發現,某間小學的伊斯蘭移民子女相當多的時候,可能就不傾向讓小朋友來這間,而選擇去其他間所謂白人較多的學校註冊。就居住環境而言,當一個新興社區中的某些建築陸續住進穆斯林時,所謂的荷蘭白人家庭自然也不會選擇在此買房或租房。久而久之,一個穆斯林的社區便形成了。 ↩
- 提奧‧梵谷曾和一位索馬利亞裔的荷蘭女權主義者阿里(Ayaan Hirsi Ali)共同製作一部名為「服從」(submission)的10分鐘影片,講述女性在伊斯蘭社會的低下地位,以及受到諸多的暴力對待行為。另外,他的曾祖父的哥哥,其實就是著名的畫家文森‧梵谷(Vincent van Gogh)。 ↩
- 屬於極右翼保守派的麗塔‧費爾東克,一向以手腕強硬著稱,也獲得鐵娘子麗塔(IJzeren Rita)的稱號。例如,她曾經於2006年時,提出一項要立法規定「人們在公共場應該說荷蘭語」的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