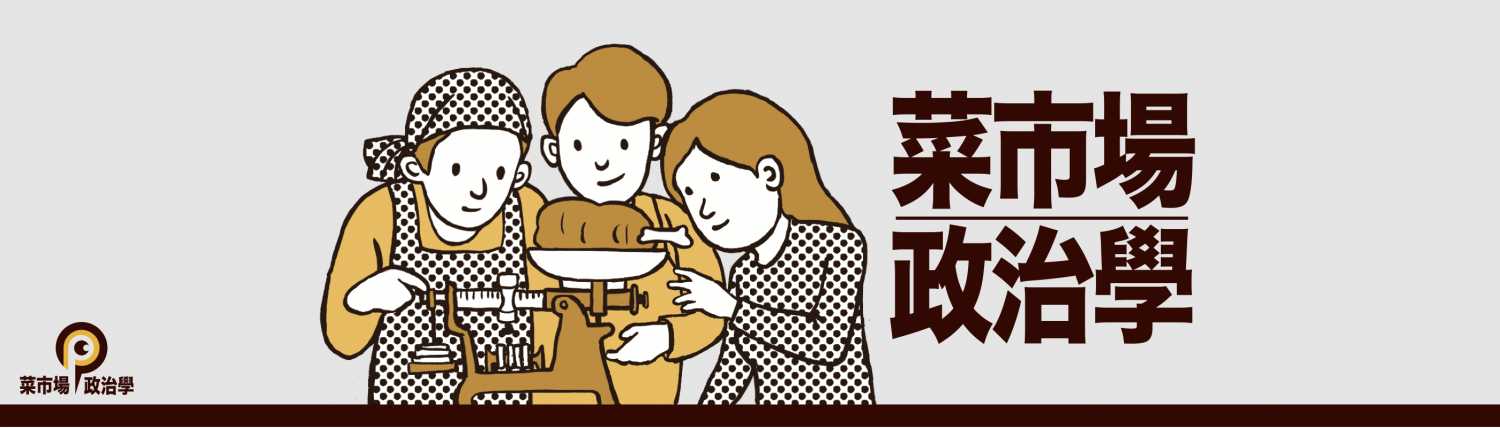◎普麟/美國杜蘭大學政治學博士生
※本文改寫自作者未發表文章〈Repression, State Violence, and Infilt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KMT Regime and Security Agencies During Taiwan’s White Terror Period〉的部份內容。如果對此研究主題有興趣可參考Geddes, Barbara, Erica Frantz & Joseph Wright. 2018. “Double-Edged Swords: Specialized Institutions for Monitoring and Coercion.” How Dictatorships Work: Power, Personalization, and Collap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4-174.
前言
日前,民進黨籍立委黃國書被媒體報導過去曾擔任過國民黨政權的「線民」,協助威權時期的調查局監控反對運動人士,最近又有週刊報導台南市長黃偉哲「疑似」為促轉會公布檔案當中的某位線民,可能曾經在大學期間負責監控社團同學。這些新聞讓線民、情治機關與轉型正義等關鍵字成為近期台灣社會的熱門話題。
事實上,無論是在民主國家或威權國家,政府皆需要透過情治機關來蒐集情報以維持國家安全。雖然相關議題可公開研究的資料不多,但仍受到不少政治學者的關注。到底政治科學家是如何研究情治機關呢?情治機關的運作與政治、統治者又有什麼關係呢?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
在民主國家,情治機關與軍隊理論上都須要服從民選政府的領導、依據法治原則行事,以及接受來自國會與媒體的監督。然而,威權國家的情治單位則是為了鞏固獨裁者的統治,其運作邏輯自然不同於民主國家。在過去二十年來,從事威權政治研究的政治學者最主要想解答的問題之一就是:在缺乏民主選舉與廣泛民意基礎的情況下,威權政權要如何維持政權的穩定與存續呢?
事實上,身為獨裁者很容易缺乏安全感,不僅要提防身邊其它政治菁英、軍事將領的造反或政變,還要擔心來自社會大眾的抗議、暴動,甚至是革命。雖然獨裁者可以掌握軍隊,在政權建立初期透過暴力鎮壓 (repression)來壓制反對勢力,但國家與經濟如果要能長遠發展,社會就不能一直處於衝突與動盪之中。於是,當代有越來越多的威權政權選擇透過暴力程度較低的攏絡 (co-optation)、提升正當性 (legitimation)等方式來維持有效且穩定的統治,例如建立有限的選舉制度,或是大力發展經濟。無論是面對來自統治階層其他菁英的爭權或是底層群眾的挑戰,獨裁者都需要能夠掌握相關資訊。因此,情治機關的誕生就成為了協助獨裁者蒐集國內外情報、對內進行秘密鎮壓與監控,進一步維持社會控制的主要工具之一。但是,要如何有效掌握與動用情治機關仍舊是讓獨裁者「頭痛」的問題,這也成為了政治學者研究的題目。
獨裁者與秘密警察
情治機關在威權國家主要負責政權的內部安全,但其執勤的秘密特性又有別於維持社會治安的警察,因此情治人員在英文文獻又被稱為是秘密警察 (secret police)。再者,由於情治機關與軍隊皆屬於安全部門 (security sector),並得以執行強制力,所以也被稱為是強制機構 (coercive institutions)。雖然研究指出,強制能力 (coercive capacity)與政權凝聚力(cohesion)越高的威權國家對於其維持統治越有利 (Way & Levitsky 2006; Wang 2014)。但是對於獨裁者而言,如果給予其過於充足的資源與能力,雖然可以強力壓制社會內部的反對勢力,但又會擔心其勢力龐大反過來推翻政權;但如果為了降低政變的風險而減少安全部門的資源,又可能無法有效完成壓制內部異議者的任務,這也成為了獨裁者掌握強制機構時所面臨的兩難(dictator’s dilemma)。
電影《竊聽風暴》劇照
圖片來源:IMDB
此時,獨裁者就要清楚地知道他的主要威脅是誰。Greitens (2016)指出,如果獨裁者認為他的最主要威脅是來自於統治階層其它的菁英,那他就會傾向將強制機構分散成多個部門,以降低某一單位獨大而威脅到政權的潛在風險;假使獨裁者認為對於政權存續最主要的威脅來自社會的反對勢力,則他就會將情治機關設計成單一制,且成員出身會盡量廣納社會各階層,以有效掌握社會內部的情報。同時,強制機構的設計也會進一步影響威權政權的暴力程度。分散式的情治機關設計由於缺乏統一的領導單位,各機關彼此會因為競爭情報而鬥爭;此時如果秘密警察成員性質(相較於社會整體)的多元程度較低,在執行任務時就更容易大肆鎮壓與濫殺,暴力程度也會隨之上升。相反的,單一制的情治機關則可以避免上述問題,在壓制反對勢力時的暴力程度也會相對較低。1。
不過,即便同樣是面臨反對勢力的威脅,一黨制的威權政權在調整情治機關的組織設計與人員部署時仍會有不同的選擇。Thomson (2020)就指出波蘭共產黨(波共)與東德在面對反對運動興起以及隨之調整情治機關規模時,卻做出不同的選擇。例如在後史達林時期,由於波共領導階層與情治機關對於政策方向出現分歧,因此波共領導人就選擇限制秘密警察的規模與人數,以降低情治機關首長政變或坐大的可能;反之,東德並未發生類似的問題,所以東德領導人就得以大力擴張秘密警察史塔西 (Stasi)的規模以加強對社會的監控。也由於波共秘密警察的規模受到限制,導致其在1950年代之後必須仰賴暴力程度較高的鎮壓手段來維持社會控制,相反的東德政權則以大規模監控來取代暴力鎮壓。
情報能力與線民
雖然擴大秘密警察的人數與規模的確可以讓獨裁政權更能牢牢控制社會,但其人事成本也會成為龐大的負擔,因此透過金錢報酬等方式在社會各階層、團體中收買線民就成為情治機關最能有效滲透社會的方式之一。以東德為例,在其共黨政權垮台前夕,情治機關史塔西竟擁有超過18萬名的線民,數量是其秘密警察人數的兩倍;換句話說,平均每一百個東德人就至少有一人是史塔西的線民。
電影《竊聽風暴》劇照
圖片來源:IMDB
為什麼威權政權會那麼需要仰賴線民呢?簡單來說,線民的部署反映出威權政權對於社會的滲透(infiltration)。線民的數量越多、分布越廣,代表著情治機關的情報能力 (intelligence capacity)也越強,政權對於反對勢力、社團所能掌握的資訊也會越多、越精準,甚至更有能力在反對組織內部進行分化、破壞 (Nalepa & Pop-Eleches 2021)。換言之,獨裁者對於社會能夠掌握的情報越多,就可以對來自反對運動的威脅提前做準備,越有利於維持政權穩定,並影響其鎮壓的模式與暴力程度。
當情治機關在執行鎮壓行動或大規模搜捕任務時,其過程非常類似內戰中的政治暴力邏輯,也就是當政府的武裝部隊擁有越完整的情報,就更有利於鎮壓與搜捕反叛軍。所以,對於一支情報能力較差的部隊就容易傾向採取無差別鎮壓(indiscriminate repression),以免有漏網之魚;反之,情報能力較強的部隊就會使用選擇性鎮壓 (selective repression),精準打擊反對勢力的成員,其暴力程度也會降低 (Kalyvas 2006)。2。Dimitrov & Sassoon (2014)也認為在後史達林時代的保加利亞,其共黨政權就透過擴大招募線民的方式讓領導人能夠更精準掌握社會內部的資訊,鎮壓手段也就從過去的無差別鎮壓轉而使用選擇性鎮壓,國家暴力程度也隨之下降,這樣的研究成果也與上述提到的Kalyvas (2006)與Thomson (2020)非常相似。反之,情報能力差的部隊或情治機關,就越有可能透過刑求的方式來從被逮捕的反叛軍或反對組織成員汲取情報,進一步導致濫捕、濫殺的可能,政治暴力程度也隨之提高 (Winward 2020)。
檔案開放的兩難
獨裁統治下的情治機關研究在整個比較政治研究領域(相較於鎮壓、政變或內戰)仍算是相對小眾的題目,而資料的取得也影響此一主題的研究能否順利完成的主要因素。雖然如此,但從最近刊出的期刊文章就可以發現,相關的題目無論是在案例挑選或是研究方法上皆越來越多元也具有啟發性。例如以檔案研究來探討東德的史塔西在1980年代如何招募阿拉伯裔學生成為線人來執行情蒐任務 (Hoffmann 2021),或是透過量化統計方式來研究超過四千多名阿根廷威權時期官員的資料,以瞭解情治人員在機關中的晉升與發展。然而,無論是採取何種研究途徑或方法,對於威權時期的鎮壓、國家暴力與情治機關等主題的研究都相當依賴過去政府檔案的開放。
在中東歐國家,由於前共黨政權垮台之後,原本的秘密警察機關也隨之解散或重組,研究者也才能夠取得相對完整的檔案資料來進行分析。在台灣,由於民主轉型的進程是由國民黨政權所主導,雖然過程較為和平,但也讓威權時期的政黨菁英及其繼承人得以直接在民主體制下進行選舉和政治參與,間接導致轉型正義在推動的過程遇到許多困難與阻礙,其中也包含過去威權政權的官方檔案徵集與移交。不過,促轉會仍透過有限的檔案統整出以政治受難者判決資料為基礎的「轉型正義資料庫」,並與專家學者合作並對過去的壓迫體制與圖像進行研究。3。
過去的情治機關檔案要如何開放,一直是新興民主國家的難題。像是過去波蘭就曾因為檔案開放之後,大眾才發現有部分的原反對勢力國會議員竟然曾擔任過共黨政權的線民,進而引發政治風暴。4由於台灣現階段對於檔案開放仍缺乏適當的處置方式,不但難以對威權時期加害者進行咎責,未來台灣仍有可能會因為有過去的線民或協力者被媒體曝光,使得檔案開放淪為政治攻擊的工具,反而引起社會內部的互相猜忌,這點或許是在研究之外更值得整個社會一同思考的議題。
*本站轉型正義專題文章集
參考資料
Dimitrov, Martin K. & Joseph Sassoon. 2014. “State Security, Information, and Repressio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6(2): 3-31.
Greitens, Sheena Chestnut. 2016. Dictators and Their Secret Police: Coercive Institutions and State Vio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ffmann, Sophia. 2021. “Arab students and the Stasi: Agents and objects of intelligence.” Security Dialogue 52(1): 62-78.
Kalyvas, Stathis N. 2006. The Logic of Violence in Civil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alepa, Monika & Grigore Pop-Eleches. 2021. “Authoritarian Infiltration of Organization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Politics, forthcoming.
Scharpf, Adam & Christian Gläßel. 2020. “Why Underachievers Dominate Secret Police Organizations: Evidence from Autocratic Argent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4(4): 791-806.
Thomson, Henry. 2020. “The Authoritarian Governor’s Dilemma: Controlling the Secret Police in Socialist Poland and East Germany.” in Abbott, Zangl, Snidal & Genschel (Eds.), The Governor’s Dilemma: Indirect Governance Beyond Principals and Agen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9-77.
Wang, Yuhua. 2014. “Coercive capacity and the durabili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stat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7(1): 13-25.
Way, Lucan A. & Steven Levitsky. 2006. “The dynamics of autocratic coercion after the Cold War.”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9(3): 387-410.
Winward, Mark. 2021. “Intelligence Capacity and Mass Violence: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4(3/4): 1-32.
※注釋
- 該書的詳細介紹可以參考菜市場政治學的文章〈獨裁者與他們的祕密警察:國家強制機構與暴力行為的比較分析〉 ↩
- 關於內戰的政治暴力邏輯,菜市場政治學的文章〈敵人、罪犯與病患(上):國家暴力與威權統治下的三種鎮壓方式〉有更詳細的介紹 ↩
- 報告書與研究成果請參考促轉會網站,網址:https://www.tjc.gov.tw/ ↩
- 延伸閱讀:《衣櫃中的骷顱》:東歐轉型正義困境與面對歷史真相的艱難。https://whogovernstw.org/2016/03/23/chinghsuansu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