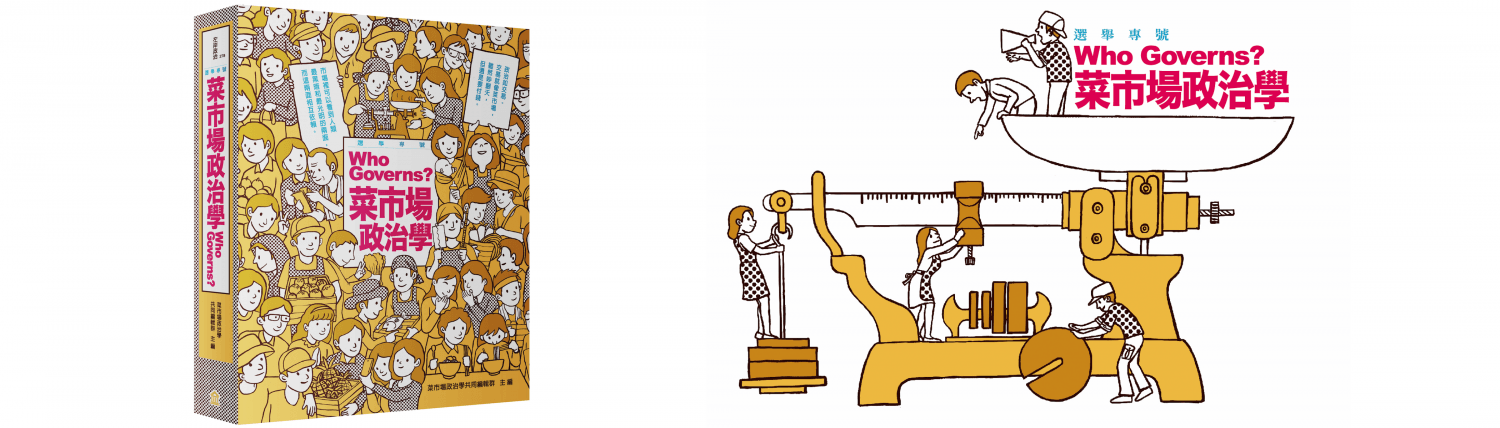◎簡宏逸/波鴻魯爾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作者簡介:簡宏逸從2022年2月起參與波鴻魯爾大學的聯合研究計畫「臺灣做頭陣:在全球大勢挑戰中的地方創新」,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在該計畫中,他研究臺灣的近代教育體系與其對臺灣近代化的貢獻。他在2017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並曾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共同編著有《圖說臺北師範校史》(2013、2016),並以筆名「黃恐龍」發表《野生的太陽花》(2014)。
2022年四月中旬,雷瑪麗博士(Dr. Josie-Marie Perkuhn)和筆者在Taiwan Insight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漢學參與臺灣研究的議題。我們的初衷是「拋磚引玉」以促進討論。隨後,我們粗淺的意見得到王德育教授和Christopher H. Achen教授寶貴的意見,雖然他們的立場和我們相反。他們也將回應翻譯成華語,發表在《菜市場政治學》,引發了更多的討論。我樂見此發展,但也發現部分讀者,特別是臺灣學者們對我們的看法有一點誤解。因此,我必須回答王教授和Achen教授的挑戰。
我的回應基於自己的經驗和觀察,所以我想獨自撰寫這篇回應,並副知雷瑪麗博士。我也把「漢學」(sinology)當作「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的同義詞。這兩個詞表示了兩種不同研究取徑,但他們的區別在這次的討論中已經變得模糊了。以下我將討論臺灣研究在高等教育機構中的定位,因為要是沒有新加入的研究者,該學科便無法存活。我也將藉此進一步闡釋臺灣研究中「基礎建設」的概念。至於臺灣研究的理論框架是另一個大哉問,這篇回應可能難以承載。
臺灣意識的高漲不保證臺灣研究的地位
在王教授和Achen教授的回應中,最強力的論證是引用臺灣認同的成長來說明臺灣研究應該被當作獨立領域看待。不過臺灣研究這個學科在臺灣的發展並不樂觀,我在臺灣的觀察可說正好相反。
我本身就是2000年代臺灣認同高漲之下的產物。當我於2006年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完成學士學位時,我抱持著想要研究臺灣的願望,決心返臺繼續研究所的學業。從2007年開始,我就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班,同時也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就讀。同時就讀兩所學校,讓我有機會修讀更多臺灣相關的課程。2017年,我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畢業取得博士學位。我的碩士和博士學位都來自臺灣研究系所。現在我的專業領域是早期臺灣史研究。
從2007年到2017年,儘管臺灣認同持續上升,我也見證了臺灣研究系所的興衰,在臺灣文學領域尤然。2011年和2015年有中興大學和中正大學的臺灣文學研究所改名,以藉此吸引更多學生就讀。中山醫學大學臺文系也在2016年停辦。近年來,臺灣文學學者也認為華語語系理論(Sinophone theory)能為「臺灣內部的人文研究帶來更新,促進臺灣人文研究的國際化,並增進臺灣人文研究的國際能見度。」他們可是正面擁抱「Sino-」這個詞綴!另一方面,儘管最近幾年臺灣研究系所的數量保持穩定,但其中許多系所都面臨報名人數減少,畢業生也在就業市場面臨嚴峻挑戰。這些困難很少被那些在臺灣研究中功成名就的學者所理解。
在臺灣教育部的統計中,專攻臺灣研究的系所可分成兩類:1.主修文學、文化、語言的「臺文」,以及2.主修歷史的「臺史」。奇怪的是,臺灣文化和文學的的系所數量不少,但在臺灣的大學中只有兩個臺灣史研究所。我從碩一就開始思考這個數量不均的問題。一個可能的答案是,1990年代臺灣文學研究崛起之時,臺灣文學不是中文系可以接納的學科,所以臺灣文學研究的先驅者感到需要進行根本的變革,建立和中國文學相異的臺灣文學研究系所。他們從1990年代起開始倡議設立臺灣文學系所,導致了2000年代臺灣文學系所的大幅成長。
另一方面,臺灣史在歷史系所內紮根的過程,採取了比較溫和的取徑。1987年解嚴之後,歷史系所開設的臺灣史課程逐漸增加,新成立的系所也強調臺灣史研究,導致研究臺灣史的碩士論文在1990年代快速增加。這些都發生在2004年兩所臺灣史研究所創設之前。雖然現在臺灣的大學中只有兩間臺灣史研究所,但沒有一個歷史系可以在其課程中忽略臺灣史。過去20年,歷史系培養的臺灣史專家比兩個臺灣史研究所培養的還要多。我們可以從臺灣史發展學到的經驗是從既有基礎上成長的重要性,也是系所在高等教育危機的風暴中生存的關鍵。我相信這個經驗適用於臺灣與海外的高等教育機構。
進一步說明何謂「基礎建設」
請注意,我從未主張將臺灣研究「合併」進漢學研究,這是王教授和Achen教授的假設性問題,用以導出臺灣認同的高漲,以支持他們認為臺灣研究應作為獨立學科的意見。我在前文已經回應此一意見。我在最初的提議中所說的是,漢學可以扮演中介人的角色,降低語言、文化、學科畛域上的障礙,並將臺灣研究傳播給未來的世代。王教授和Achen教授也對雷瑪麗博士和我所主張的「基礎建設」感到困惑,但我們其實已經將「基礎建設」定義為「讓新加入臺灣研究的人成長的基礎」。
我想將「基礎建設」的討論局限於臺灣以外的大學,因為臺灣研究在這些海外高等教育機構中面臨更多的挑戰。除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臺灣研究學程相對有組織,其他大多數臺灣研究「學程」其實僅是一些與臺灣有關的課程。在我的母校華盛頓大學,臺灣研究學程(Taiwan Studies Program)在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中,既不是主修也不是輔修。如果我今天就讀於華盛頓大學,我可能還是只能主修亞洲研究或輔修中國研究以完成我的學士學位。我無意指責世界各地在大學裡推動臺灣研究學程的努力,但臺灣研究在國際高等教育場域的不成熟,是我們不願面對的真相。
因此,我們有必要討論需要什麼樣的基礎建設來幫助對臺灣有興趣的學者進入這個領域。我認為進行臺灣研究最重要的關鍵能力是:1.認識臺灣,以及2.掌握各種臺灣語言的能力。我們不需要從頭開始建設臺灣研究學程,大多數海外臺灣研究學程的作法是在現有課程中開發新課程。每個大學都有其傳統與建置。在有漢學系的大學中,漢學系是最可用於推動臺灣研究的學科。在漢學系,學生可以在現有課程中學習漢語系語言(Sinitic languages),以及與臺灣有關的知識。我們期待臺灣研究在未來成長成一個獨立的學科,但現在他仍需要漢學系來培養其茁壯。
德語國家的狀況
王教授和Achen教授在他們的回應中列出了幾所大學的臺灣研究中心,認為「這些研究臺灣的學術組織,都不是設立在中國研究或漢學研究中心之下」。這個觀察符應了英美中心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看法,但在德語國家的狀況則有點不一樣。由臺灣教育部資助的「臺灣研究講座」,在德語國家的執行單位都是廣義的漢學系。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的教授們主導了杜賓根大學的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心(European Research Centre of Contemporary Taiwan)。波鴻魯爾大學由兩位漢學教授主持已有二十餘年歷史的臺灣文化與文學研究所(Research Unit for Taiwa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維也納大學的維也納臺灣研究中心也與該校漢學系有關。特里爾大學雖然沒有獨立的臺灣研究單位,但該校漢學系領導了「臺灣做頭陣:在全球大勢挑戰中的地方創新」(Taiwan als Pionier – Lokale Innovation in der Dynamik globaler Megatrends)這個三校聯合研究計畫。這些漢學系和教授為推動臺灣研究付出了巨大努力,德國和臺灣的獎助機構也都認可他們的貢獻。
我想說的是,漢學參與臺灣研究並不奇怪。國際上的臺灣研究新生需要漢學來成長。臺灣史在臺灣高等教育機構奠基的經驗表示,一門新學科需要肥沃的土壤來培養。在有漢學的國家,這門「政治不正確」的學科難免會在招收臺灣研究新人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我相信,這些學生都能區分臺灣與中國的不同,所以我們可以將臺灣研究的未來託付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