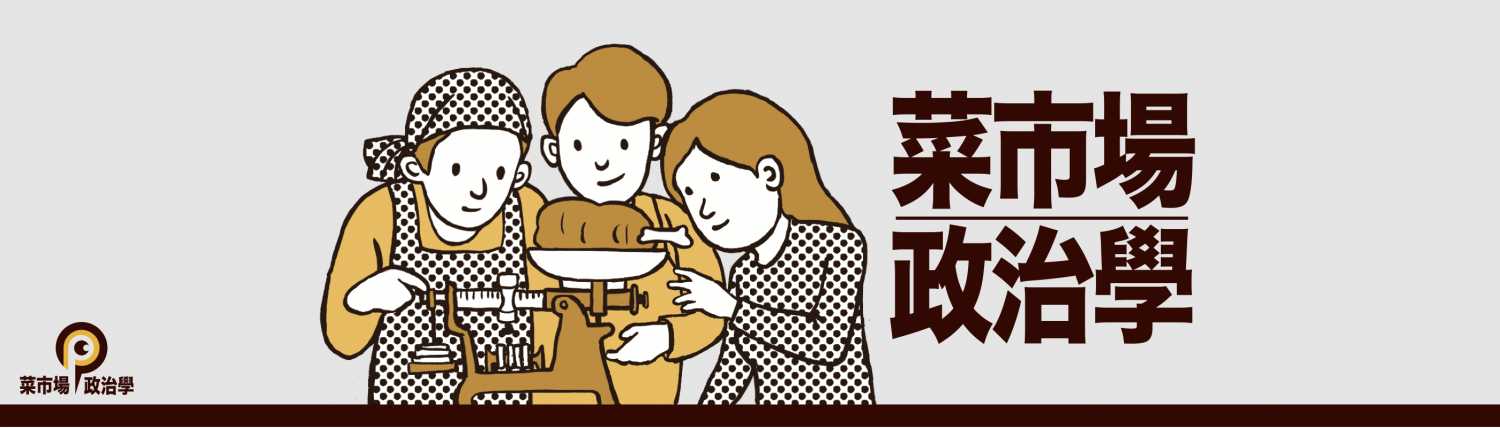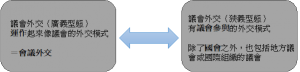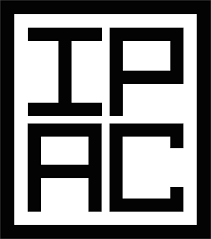◎曹晉華(東海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相較於傳統的外交方式,議會外交(parliamentary diplomacy)是國際交流的一項新興趨勢,其中,由國會進行的議會外交(也就是國會外交)是主要的型態。[1]對於國會外交,我們可以很快地聯想到,之前美國眾議院議長與捷克參議院議長訪問台灣的案例。但具體而言,什麼是國會外交呢?它為何對台灣重要?由於「國會」專指國家級的議會,而「議會」是一個比較大的通稱,因此讓我們先從議會外交開始談起。
學者Stavridis(2019: 235)將議會外交定義為:「任何具有外交性質的宣言、行動或活動,至少涉及一位議會行為者,並試圖對某一特定的國際議題(或具有國際涵義的內部議題)產生影響」。[2]不過,在一開始,議會外交並不是這個意思。「議會外交」這個用詞在1950年代第一次出現,起初指涉「政府間談判過程中的某些議會程序,目的是促進傳統外交」(Majidi, 2021: 318)。在當時,外交主要由行政部門負責,國會能參與的空間有限。直到21世紀之後,議會外交才比較常被用來描述各國議會之間的外交互動,而與傳統上由政府或外交官主導的外交模式產生區隔。
對於台灣而言,雖然我國缺乏廣泛的正式外交承認,但近幾年來在議會外交方面已取得一些豐厚成果。相較於傳統的外交模式,議會外交具有彈性較高、較低的官方色彩、接觸面向較廣等特徵。此外,近年來國際上也興起一波「議會化」的趨勢,這包含國際組織以及對外關係兩個面向。國際組織的議會化,是指議會的跨國串連,而對外關係的議會化,則代表議會在對外關係中的角色,有了更多主動出擊或參與的空間。以下,本文將介紹議會外交的概念起源、相對於傳統外交的優勢,以及台灣近幾年在這方面取得的成果。
議會外交的概念起源
如果從英文Parliamentary Diplomacy來理解,議會外交其實就是「議會(式)的外交」。廣義上,它可以是在方法、程序或決策上與議會相似的外交模式,狹義上,它也可能指涉有議會成員參與的外交行動。
有學者將議會外交的起源追溯至西元前4世紀的希臘城邦時期(Jaskiernia, 2022; Cooper, Jorge & Ramesh, 2013: 21)。當時,雅典與波斯為了解決衝突爭端,而開了八次會議以保證領土現狀,並訂定雙邊的行為規則。上述各國派遣代表團,針對特定議題集會討論的模式被稱為「會議外交」(conference diplomacy)。
直到近代,各國透過會議而解決國際爭端的方式仍然存在,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便是一個代表性的案例,該會議的背景是歐洲各國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為了恢復國際秩序並尋求各國間的權力平衡,而召開的一系列會議(Launsky-Tieffenthal, 2014)。在維也納會議之前,國家間主要是以派遣使節的方式進行外交,因此,這種多國參與、相對密集且面對面的談判溝通方式,可說是一項創舉。如果說維也納會議是以衝突善後為導向,那麼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則是第一個嘗試將「會議外交」制度化的國際組織。在國際聯盟(以及後來的聯合國)中,由於各國的代表團都是會議的成員,並且有固定的開會、投票程序,就像議會一樣,所以是一種議會結構(parliamentary structure)的外交模式(Götz, 2005: 264-265)。在今日,在許多國際組織或多邊機制中,我們也經常能夠看到各國派遣代表團,針對國際事務共聚商討,而討論的事項亦不侷限在國際衝突議題。
維也納會議 Congress of Vienna
綜上所述,「會議外交」是理解國際政治的一項重要概念,它可以被理解為「運作起來像議會」的外交模式,所以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它被稱為「議會外交」。然而,這和今天我們普遍認知的「議會外交」仍有很大的不同。在21世紀後的大多數情況下,議會外交多用來描述各國議會之間的外交互動,而很大程度上,這裡指的是國家層級的議會。因此,這是一種以議會為代理人(parliamentary agent)的外交模式(Götz, 2005: 264-265)。在這種模式下,議會成員(例如國會議員或議長)是外交的行為主體,而有別於由政府或外交官主導的傳統外交。
國會外交的優勢
傳統上,當我們談到「外交」時,指的是國家之間的互動,例如外交承認、簽署協議或是外交照會。相較於其他國內政策,外交常常被視為是政府的特殊領域,國會能夠影響的空間有限(e.g. 施正鋒,2009:172-173)。不過,隨著全球化、交通與資訊技術革新以及環境、人權與恐怖主義等多元議題的加入,當代的國際互動顯得更加多面向與複雜。在當代國際政治中,國家並非唯一的行為者,有越來越多的非國家行為者(例如NGOs、地方政府或跨國企業)或國際組織參與在其中。正是在此趨勢下,國會外交在國際舞台的重要性逐漸受到重視。
相較於傳統的國家外交(state diplomacy),國會外交存在一些優勢。國會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但又不像行政部門那樣具有官僚色彩。在許多複雜難解的情境中,國會外交能夠發揮緩和衝突、促進對話的功能(Zamfir, 2019: 7-8)。當然,國會外交也不是在這麼「硬」的場合才能發揮功能。國會外交可以是技術、文化或民間合作等「軟實力」的交流,透過產業參訪、會面、簽訂備忘錄的方式來促進跨國合作。甚至,議員之間個人關係的建立,也會是促進雙邊交流的方式之一。
即便各國的國會議員並不具有外交使節或代表的正式身份,但藉由國會外交的機會,政府可試探被訪國的外交態度(Jaskiernia, 2022: 88)。反之,被訪國也能夠瞭解他國議員們的立場。有時,國會外交也能對外交政策起到關鍵影響。隨著民主的擴散與深化,各國議會對於外交政策有了更多的監督空間。在一些情況下,國會甚至成為外交的主要行為者。由於在民主國家中,國會往往掌握外交決策、預算的審查權,因此直接與國會議員溝通,也能夠降低溝通與談判的成本,並且強化政府外交舉措的正當性。Stavridis認為,這些現象可以說是一種「國際事務議會化」的新興趨勢(2019: 245)。
雖然國家之間的國會成員的互訪相當常見,但國會外交的對象並不侷限於國會,其他國家的行政部門、民間團體或者是國際組織都可能是國會外交的對象。如前文所指出,議會外交可以是廣義上「運作起來像議會」的外交(會議外交),也可以是狹義上「有議會參與」的外交,而後者能夠更加頻繁、非正式、多面向的進行,進而為傳統的國家外交助攻。以下,本文將透過一些國際組織的案例,說明議會外交在這兩個面向(狹義與廣義)上的結合。
圖1 議會外交概念示意圖
既是議會,也是國際組織
除了國家層級的議會之外,由各國議會所組成的國際組織或多邊機制,也是國際政治的重要行為者或場域。成立於1889年的各國議會聯盟(IPU),是第一個常設性的跨國議會組織(Stavridis, 2021: 230)。IPU在促進國際對話與各國議會運作方面發揮積極功能,可說是議會界的聯合國。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IPU)
除了IPU之外,目前國際上也有一些區域性國際組織另外設置「議會」,例如阿拉伯議會(2004年成立,為阿拉伯國家聯盟立法機構)[3]、安地斯議會(安地斯共同體的立法機構)、中美洲議會等。這些由鄰近國家議會組成的國際組織,由於成員國在地緣、文化、政治上有較深厚的連結,因此在區域發展與和平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中美洲暨加勒比海盆地國會議長論壇(FOPREL)是跨國議會外交的另一例子。與上述區域性國際組織不同,FOPREL是由各國議會組成的多邊機制。目前,我國(立法院)為FOPREL的永久觀察員,並且有半數邦交國位於此區域。[4]
此外,2020年成立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對我國擴展國際空間具有相當重要性。IPAC由歐洲議會與33個國家的國會議員組成,旨在透過立法者間的合作,協助各國擬定一致且適切的對中政策。IPAC關注的議題廣泛,包括維護國際秩序、人權保護、貿易公平、強化安全以及保障國家的完整性,而對於各國而言,這些也是面對中國挑戰時必須考量的關鍵政策領域。總結來說,國際組織或者多邊機制是議會外交重要的一環。隨著國際組織的重要性增加,這些國際組織的成員(各國議會)或是議員,也有可能反過來影響該國政策的制定(Jaskiernia, 2022: 95)。
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
台灣的國會外交:近期的成果與展望
雖然,我國缺乏廣泛的正式外交承認,但近幾年來在「國會外交」方面已取得一些豐厚成果。以第10屆立法院為例(2020-2024),截至2023年8月底,立法院共接待了來自38個國家的114個訪團,合計1,386位來賓。這些訪團包括: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2022年)、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2020年),以及美國國會跨黨派議員(多次)等。為呼應「國會外交」對於臺灣的重要性,並且將延續既有之成果,立法院在去年成立「國際事務處」,專責處理國會外交事宜。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前文提到的「對華政策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對我國立場相當友善,但我國目前仍並非該聯盟的成員。按照該組織規定,各國議會需要有兩個主要政黨的同意才能成為會員(共同主席)。然而,由於上一屆國會中國國民黨拒絕加入,因此目前台灣並不是IPAC的共同主席。即便如此,基於台灣在地緣政治與兩岸關係上的特殊地位,我國仍有立委受邀參加2022年會,並主持2023年會中的臺灣議題論壇。
根據立法院官網資料,第10屆立法院共成立73個議題、區域或特定國家相關的「國會聯誼會」。在法制上,國會聯誼會屬於非正式編制的國會次級團體,由跨黨派的立法委員組成。事實上,無論是彈性但仍具政治性的國會外交或是各種官方或民間的交流,都有助於增加臺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比如,國會聯誼會也能夠與行政部門或相關民間團體保持緊密連結,發揮「政治樞紐」的功能。[5]
總結來看,外交是長期累積的過程,而對於台灣而言,國會外交可以作為傳統外交的輔助,促進與各國實質關係的發展。隨著新一屆立法院開議,立法院長與立委們的外交角色也備受關注。國會外交的優勢,在於彈性、多面向與官方色彩較低,同時也肩負著民意的付託與期望。在未來四年中,國會外交與傳統外交如何產生加乘效果,是國會各黨派需要共同思考的課題。
※註腳
[1] 在英文中,內閣制國家的國會通常為Parliament,總統制國會則稱之為Congress。有趣的是,雖然有學者以”Congressional Diplomacy”來稱呼總統制國家的議會外交,但整體而言,”Parliamentary Diplomacy”是更常被使用且通用的詞彙(Stavridis, 2019: 234)。此外,臺灣習慣將Parliamentary Diplomacy翻譯為「國會外交」,這在描述「國家層級議會」的情況下是準確的,但可能忽略了議會外交的其他面向(如國際組織、多邊機制或各國地方層級議會間的交流)。在以下的內容中,本文將依據論述脈絡而交替使用國會(外交)與議會(外交),前者強調國會作為外交的參與者,後者則指涉議會的結構、功能或者泛稱。
[2] Any declaration, action or activity of a diplomatic nature that involves at least one parliamentary actor, and which tries to impact on a particular international issue (or an internal one with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
[3] 「阿拉伯議會」與「阿拉伯各國議會聯盟」(Arab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是兩個不同的國際組織。
[4] 我國也曾經是中美洲議會(PARLACEN)的常駐觀察員,直到2023年8月中美洲議會批准中國取代台灣的觀察員地位。根據蘇彥斌(2023)的整理與分析,目前我國以中華民國或台灣為名號參與,並且為「正式會員」的國際組織共有15個,以「觀察員」身份參與的國際組織共有7個;有鑒於取消觀察員身份較容易,而撤銷正式會籍較難,因此我國政府應審慎關注這7個國際組織的相關動態。此外,須註明的是,並不是所有該區域的議會都有加入FOPREL。
[5] 當然,在其他國家的國會中,也有可能成立「友台小組」,例如:如日華議員懇談會、美國「國會台灣連線」、法國「參議院友台小組」等。此外,歐洲議會內也設有友台小組,有關歐洲議會友台小組之功能與運作,詳可見張福昌(2009)。
※參考文獻
Cooper, A., Jorge H., and Ramesh T.(2013). Introduction: The Challenges of 21st-Century Diplomacy, in Andrew Cooper, Jorge Heine, and Ramesh Thaku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Diplomacy.
Götz, N. (2005). On the Origins of “Parliamentary Diplomacy”: Scandinavian “Bloc Politics” and Delegation Policy in the League of Nation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0(3), 263–279.
Jaskiernia, J. (2022). Parliamentary Diplomacy – A New Dimension of Contemporary Parliamentarism. Studia Iuridica Lublinensia, 31(5), 85-101.
Launsky-Tieffenthal, P. (2014). Conference diplomacy from Vienna to New York: A personal reflection. UN Chronicle, 51(3), 4-8.
Majidi, M. R. (2021). Parliamentary Diplomacy: Its Evolution and Ro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anian Review of Foreign Affairs, 12(34), 306-329.
Stavridis, S. (2021). Parliamentary Diplomacy: A Review Artic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rliamentary Studies, 1(2), 227-269.
Zamfir, I. (2019). Connecting parliamentary and executive diplomacy at EU and Member State level.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施正鋒(2009)。美國國會外交與議長外交的初探。台灣國際研究季刊,5(4),169-183。
張福昌(2009)。台歐關係的基石:“歐洲議會友台小組”的建構與功能。東吳政治學報,27(4),55-114。
蘇彥斌(2023)。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所用名稱之分析。遠景論壇。網址:https://www.pf.org.tw/tw/pfch/12-103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