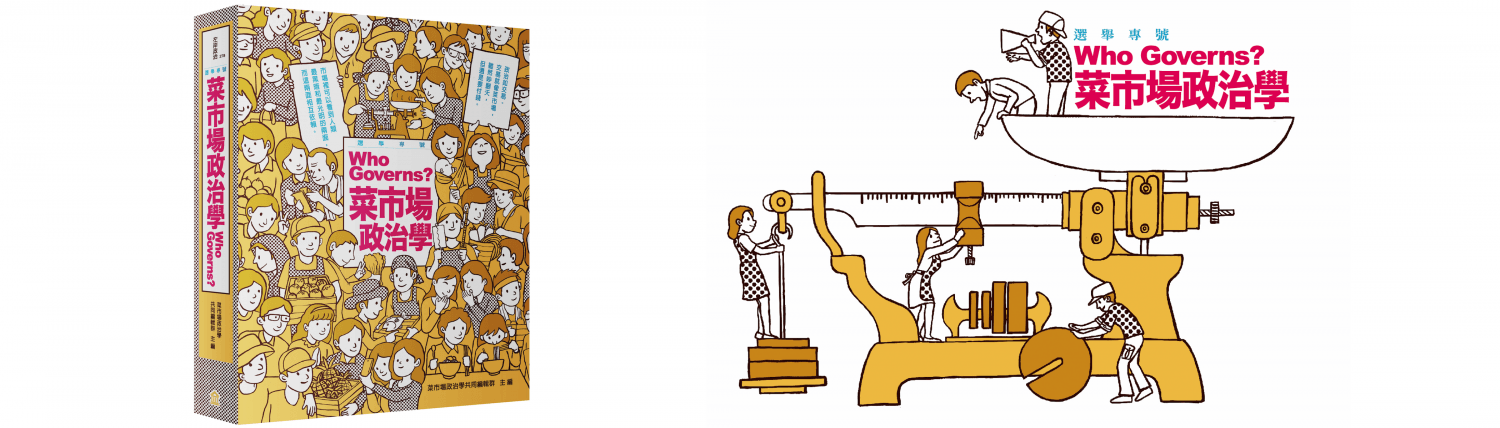◎陳方隅/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書名:《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
作者:丹.史萊特、 黃一莊
譯者:閻紀宇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4/05/21
本書主要論證亞洲國家民主化的路徑,解釋為什麼有些國家民主化成功,有些卻仍維持威權統治。這是比較政治研究當中一個非常顯著且仍然爭辯中的主題,作者黃一莊(Joseph Wong)及史萊特(Dan Slater)兩位教授長期研究亞洲政治,他們具有非常創新的理論企圖、也確實提出了有潛力挑戰既存民主化理論的新論述。這本書剛出版時就引起學界不少的討論,其中的特別之處除了引介的案例全都出自亞洲,以及他們從現代化理論的「經濟發展」因素出發,透過書中論證的由上而下式、政治菁英主導的民主化理論,推導出了一項不同以往的因果機制。
主要論點:菁英主導的民主化
黃一莊與史萊特認為,民主化的啟動是掌握政治權力的菁英們主動為之,目的是確保他們對政治議程的掌控,以此制定對自己有利的制度,以延續政治權力。當政治菁英們評估環境的狀況(具體可以從經濟景氣好壞、群眾抗爭頻率與規模大小、地緣政治變遷,以及部分選舉結果來觀察)開始出現一些警訊、威權統治開始有些動搖、獨裁手段不再是無往不利的時候(作者稱為接收到「凶險訊號」),獨裁政權的統治菁英們會開始考慮釋放部分政治權力、甚至是民主化的可能性,又或者是要加強控制;而此時他們如果也感知到了「安心訊號」,也就是環境讓這些菁英們認為即使發生民主化,原本的統治階層也不會大難臨頭、仍然可以掌控局面,然後當凶險訊號與安心訊號交替出現,作者們稱之為「苦澀甜蜜點」(bittersweet spot),這些菁英們很可能就會憑著政權所保有的強勢實力(strength)來主導民主化,這樣一來在民主化之後就仍然可以維持最優勢的統治地位。
作者們透過亞洲國家十二個案例來闡述這個理論。他們把這些國家分成四大類:首先是成功民主化的日本、臺灣與南韓,稱為「發展型國家主義」(developmental statist);第二是泰國、緬甸與印尼組成的「發展型軍國主義」(developmental militarist),由於軍政府掌控權力,民主化受到很大的阻礙;第三是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所屬的「發展型不列顛」(developmental Britannia);第四則是中國、越南與柬埔寨的「發展型社會主義」(developmental socialism)。從這些案例當中,兩位作者一一檢視每個國家的政治菁英所面對到的政治狀況以及他們的抉擇──例如在中國(第四組),政治菁英們歷經六四事件這樣的大型抗議之後,因為感到政權的脆弱而更加收緊權力;而第一組的日本、臺灣和韓國,都是由政治菁英們在最具優勢時主動地參與制度改革與民主轉型,以持續掌控政治局面;第二與第三類的國家當中,這些政權往往以拖待變,錯失憑藉自身實力推動政治體制轉化的機會。
本書的特點是從區域研究的觀點出發,在各別個案的脈絡下進行歸納。若先拋開民主化理論的爭辯,本書側寫了亞洲精采的政治發展史,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一個論述完整、邏輯推演相當縝密、能夠「一般化」到不同案例的民主化理論。
主要民主化理論的回顧與定位
進一步來說,若要知道本書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民主化研究當中的位置,我們還是必須回顧過去民主化研究的幾個主要理論(請對照參閱林宗弘老師為本書所撰寫的書評,或者是筆者的一個簡單筆記,此處篇幅關係僅能簡單帶過)。首先爭辯最久的是現代化理論,即「經濟發展」導致了民主化,這是因為經濟發展會創造眾多的「中產階級」民眾,而他們會要求更多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權利。後來的文獻雖質疑這個因果關係的存在,亦提出不同類型的民主轉型路徑,但學術研究大致上可以證實,經濟發展程度和民主化機制是正相關,且經濟發展程度愈高,民主國家愈不容易出現民主倒退。
第二大類的理論是階級之爭,主要談的是不同階級行為者之間的合縱連橫,導致國家政體往不同方向發展。這類理論的代表作由摩爾(Barrington Moore)提出,他認為「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當新興資產階級出現、和舊政權下的貴族菁英相結合,最後很大的機率是藉由戰爭來掃除舊勢力(例如英格蘭內戰,又稱清教徒革命﹝Puritan Revolution﹞、法國大革命,以及美國內戰),達成民主化。從階級之爭發展而來的是「經濟不平等」理論,這是由博伊斯(Carles Boix)所開啟的辯論,他認為當經濟不平等程度愈高,平民百姓愈會想要民主化,因為他們期待民主化之後可以重新設定「重分配」的機制(例如:調整稅率),從原本掌握政經權力的菁英手中獲得更多財富。艾塞莫魯(Acemoglu)與羅賓森(Robinson)則認為,當經濟不平等的嚴重性達到特定程度之後,政治與經濟菁英都會聯手阻止民主化,因為不平等程度愈高,重分配機制將讓他們損失愈多,在此框架下,經濟不平等程度和民主化的機率呈現倒U的曲線,原本是正相關,但在經濟不平等超過了一個關鍵節點後轉為負相關。
第三大類理論的核心是國際因素,這類觀點包含杭廷頓(Huntington)所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示範效應」,以及李維茲基(Levitzki)與魏伊(Way)研究提出的論點,認為民主化的機率會直接受到與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連結所影響,當西方國家對一個威權國家的影響力愈高,該國家愈容易民主化。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理論或分類方式來解釋民主化,不過以上大概是最常被提起的民主化理論分支。
與作者商榷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題
黃一莊及史萊特兩位教授的論點即是從現代化理論出發,解釋為什麼在亞洲國家,現代化(經濟發展)不必然帶來民主化,且民主化的路徑是一種由上而下式的進程。不過,在閱讀本書時有幾個筆者認為同樣很重要的論點,很想「敲碗」作者們再提供更多的論著。首先,本書和過去的民主化理論對話比較少,尤其本書主要是提出一個由上而下式的民主化理論,除了杭廷頓在《第三波》所談到的關於政治菁英主動推行民主以掌握政治改革的主導權、避免被清算這樣的論點之外,先前還有一本重要的專著是來自哈佛大學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教授所著《保守黨與民主的誕生》(Conservative Partie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 2017),只是本書沒有在這樣的基礎上作更深入的討論。
第二,在質化研究當中,選擇案例的邏輯一定永遠都會有被批評之處,這本來就無可厚非。不過,在本書這些案例當中,香港的例子似乎會有點格格不入,因為他們並沒有自己的主權,民主化與否的決定權掌握在北京的政治菁英手中,香港人本身並沒有決定權;另外比較可惜的是菲律賓被排除在比較案例之外,作者們的解釋是認為菲律賓「威權實力與發展實力兩頭落空,根本不會有憑藉實力轉向民主這個選項」,可是這有點像是從結果回溯的觀點:從「馬可仕被趕下臺」的當下來看,經濟發展與政權實力確實都狀況欠佳,但若是往前回溯,菲律賓的獨裁政權也曾經有過高峰,和本書其他的民主化失敗案例應該都有相當的可比性才對。
第三,在分析民主化的同時,作者們似乎忽略了國際因素,例如臺灣的蔣經國推動自由化政策的過程中,很大的動機是來自美國的施壓,倒不見得是因為蔣經國對民主化進程「感到安心」。這點我們可以參照一些最新的歷史研究學術作品,例如陳翠蓮老師的《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從歷史檔案來看,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心力交瘁、內外交迫的獨裁者。舉例來說,他之所以沒有直接指派自己的兒子蔣孝武為接班人,「劉宜良案」(筆名江南)的影響至深、又或者本書和許多坊間書本皆正面評價蔣經國對「臺籍菁英」的提拔,實則背後也是正當性危機下的應對措施,更何況,他在安排接班人的時候,仍是以外省人為主,李登輝並沒有為此獲得實權。而李登輝後來透過各種方式鬥倒當權派、取得政治權力並且推行民主改革,當然也就跟蔣經國沒有關聯了。
本書在臺灣的案例當中主要分析的對象,採用蔣經國而非李登輝,這樣的選擇本身就很令人意外。綜觀臺灣的民主化歷程,由蔣經國之手助力之處少之又少,好比在解除戒嚴當下,國民黨立刻施行《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反而造成「愈解愈嚴」,根本沒有要民主化的意思。若從李登輝時期來分析,可能會更符合本書所提的菁英主導式的民主化途徑。
而在主要變數的測量方面,要比較這麼多的案例更會有不少困難,比如說,政治菁英們究竟是怎麼評估自身力量的強弱呢?當鄧小平與中共政治菁英看到天安門事件的發生,覺得自己政權「過於衰弱」而採取暴力鎮壓,然而實際上中共還是牢牢掌控著軍隊與社會。兩位作者提出很多層面來評估政權的實力強弱,然而對於統治菁英們來說,這些評估都還是很主觀,也許對統治菁英們來說,不管再怎麼強大都還是會有不安全感,又或者是即使各方面實力相對弱勢、但關鍵軍事力量就已足夠達成全面的控制。要建立一個客觀的理論解釋到底何時才是那個最剛好的「苦澀甜蜜點」,進而讓政治菁英們在最恰好的時機開始推行民主化,要確立這樣的論證,本身就不是易事。
談本書的翻譯與出版
最後要提一個很值得討論的重點:本書主要概念之一是democracy through strength 與through weakness的比較,在中文版裡面翻譯為「憑藉實力轉向民主」,我認為這樣的翻譯好像有那麼一點點的奇異感,但這不是翻譯的問題,而是英文與中文轉換的問題。不管是democracy through strength或through weakness,這兩個詞的確很難翻譯。從英文的語境來說,主詞都是democracy,行為者是整個政權,但如果翻譯成「憑藉實力轉向民主」、「因為衰落引發民主」這兩個翻譯的主詞就已經變得不一樣。「因衰退引發民主」的主詞和英文語境比較像,主詞是整個政權(被動地轉向民主),不過,「憑藉實力轉向民主」的主詞則很明顯是指統治菁英。其實strength的概念翻譯成「實力」可能也不盡然合乎原文語境,它比較像是在談獨裁者的統治強度,或者是「優勢」。當然,這些都不是翻譯的問題,而是中英文語境不同所造成的一點點理解上的註記。
總而言之,本書雖然在質化案例的詮釋以及理論建構上可能會有一些值得後續討論的空間,但這毫無疑問地是一本非常精采的作品,很適合對亞洲諸多國家民主化的進程、政治發展歷程、以及統治菁英與社會關係有興趣的讀者們來閱讀。很高興看到這部重要的作品推出中文版,我相信即使完全撇除民主化理論的學術發展脈絡,把這本書當做亞洲各國民主發展史來看,讀者們的收穫肯定也是相當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