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禹仲(中研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
書名:《名為和平的戰爭:武裝暴力與帝國時代的全球秩序》
作者: Lauren Benton
譯者:唐澄暐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4/12/04
Ubi solitudinem faciunt, pacem appellant.
他們創造一片荒蕪,卻稱之為和平。
這段話出自著名的羅馬史家塔西佗。塔西佗重述了羅馬軍隊征服蘇格蘭過程中,與喀里多尼亞聯盟軍隊交戰的過程。在交戰前夕,喀里多尼亞聯盟領袖呼籲族人們抵抗羅馬軍隊入侵發表了演說,指控了羅馬軍隊所允諾的和平,有著什麼樣的真面目。這場戰事被名為格勞庇烏山之役,羅馬軍團損傷了三百六十名的輔助軍軍士(由非羅馬公民組成、附屬於正規公民軍團的軍隊),殲滅了一萬餘名的喀里多尼亞聯盟守軍。塔西佗的岳父、時任不列顛總督的阿古利可拉正是主導了這場戰役的將領。這場戰役往往被視為羅馬征服不列顛的最後一場戰爭。那之後,羅馬人為不列顛帶來了和平。
在歷史敘事與藝文創作裡,以戰止戰的思維,往往被賦予了某種悲劇色彩。它似乎指向了主角在面對現實戰爭衝突,無可奈何以致別無選擇,從而必須背負起沉痛負擔所做出的、殘酷但從長遠看來卻是正確的抉擇。張藝謀執導的電影《英雄》講述了中國的戰國時期,當六國察覺了秦國軍事擴張的野心時,武功高強的人們如何試圖暗殺秦王以瓦解秦國的謀畫。隨著電影接近尾聲,被賦予眾望的主角與秦王碰面後,終於體察到為什麼他之前的幾位高手紛紛放下了刺殺秦王的動機。戰國是亂世,戰爭是亂世的常態,而戰爭是殘酷的。也因此,需要一勞永逸地免除戰爭,而唯一的辦法,就是結束亂世。唯一的辦法,是讓秦王打一場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也許電影的尾聲隱隱約約暗示了,真正的英雄,是那位帶有洞見、背負起殺戮罵名也甘願以戰止戰的秦王。
同樣的思維,也出現在克里斯多福.諾蘭執導的《奧本海默》裡。當波耳(Niels Bohr)獲救並出現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時,他私底下詢問奧本海默的第一個問題是「它(原子彈)的威力夠龐大嗎?」奧本海默立即反問:「龐大到足以終結二戰嗎?」波爾則澄清:「足以終結所有戰爭。」在《奧本海默》裡,核武器的殘酷足以被終結戰爭的正當性所彌補。差別在於,諾蘭在電影中導演了正當性辯護的不斷推遲,以及奧本海默最終意識到正當性永遠無法證成的遺憾。使用核武器,首先是必須用來終結納粹德國的戰爭,隨著納粹德國戰敗,目的轉為終結太平洋的戰事,而後人們希冀著其駭人後果足以終結所有的戰爭。這不斷推遲的過程,最終的終點是正當性並不存在。一如奧本海默所自承的:「人類將會意圖使用任何手中持有的武器。」
足以一勞永逸嚇阻所有戰爭的武器並不存在,一如足以消止所有戰爭的戰爭並不存在。塔西佗所陳述的,以和平為名的戰爭,本質上還是戰爭,也與其他的戰爭無異。即便戰爭帶來了和平,也不足以構成正當化戰爭的理據。
塔西佗的句子,正是本書書名的由來。《名為和平的戰爭》一書的作者勞倫.班頓是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與法學講座教授,專長是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帝國脈絡下(尤其是殖民關係)的國際法史。她長期以來的研究關懷,一直是當今國際法秩序的構築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涉及了歐洲帝國殖民擴張的政治衝突,並且正是隨著歐洲帝國試圖理解並消化這些政治衝突(並且在這些衝突中獲勝),從而得以將「國際法秩序」這麼一個有著深厚歐洲法學理論傳統的規範概念,落實為現今人們習以為常的國際秩序。這會立即帶來一個引人反思的課題,即如果現今國際法秩序生成過程中,涉及了不正當的軍事擴張與帝國壓迫,那麼人們要如何理解、解釋、甚至接受現今國際法秩序的正當性?
針對這麼一個問題,在網路輿論中,存在著一種單純的解釋。正因為現今國際法秩序的發展過程涉及了歐洲帝國的擴張與壓迫,因此現今的國際法秩序只是歐洲帝國擴張與壓迫的產物,因此這樣的秩序一來是純粹為西方帝國主義服務的遮羞布,二來是不正當且壓迫非西方世界的存在。這樣的論斷帶有過多的化約與跳躍。舉例來說,它忽視了國際法作為規範秩序,是試圖理解並排除非正當政治與軍事衝突的存在,並不是帝國擴張的產物。對於國際法秩序生成過程中,所涵蓋的政治與軍事衝突的解釋,不能單純以「這是歐洲的概念,因此必然是為歐洲利益服務」的一廂情願為依據,而是必須要以「法秩序如何面對、解釋、規範政治與軍事衝突」的角度來理解。這是班頓的研究一直以來的核心課題,而本書正是班頓最新的研究成果之一。
本書的核心課題,在於指出任何政權,當深陷政治與軍事衝突時,都會試圖訴諸特定的法秩序來解釋並正當化其之所以深陷衝突的原因,並作為政權必須採取軍事行動的理據。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政權總會尋求法秩序來為其行動做出合理的解釋,並以此作為其行動正當性的依據,與法秩序的存在就是在正當化政權的行動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情。本書所隱含的重要呼籲之一就在於,在維繫法秩序的穩定與規範性的同時,我們必須要時時謹慎於不同政權如何訴諸法秩序以正當化其政治與軍事衝突的行動的行徑。班頓以「法理政治」(legal politics)這樣的詞彙,來陳述這樣的現象。而法理政治最常見的結果,就是歐洲帝國在其擴張期間,一方面透過國際法秩序來約束戰爭,同時藉由訴諸國際法秩序來指出,帝國所參與的政治與軍事衝突,以及帝國所採取的軍事行動,並不是受國際法秩序所約束的戰爭,而是更小型的零星衝突。在這裡,必須要再次強調的是,歐洲帝國訴諸「法理政治」與其他政權訴諸「法理政治」,都是政權正當化其行動常見的行徑,但「法理政治」本身的存在與國際法秩序的正當性是沒有因果關係的兩個獨立事件。
書的研究內容,正是梳理並分析歐洲帝國如何藉由「法理政治」來強調自身的軍事行動與牽涉的政治與軍事衝突,並不是受國際法秩序所規範的戰爭,並藉此來強調其行動的正當性。這其中涉及了要如何分辨「戰爭」與「零星地域衝突」的界線。班頓在本書中指出了歐洲帝國在美洲與亞洲常見的、「法理政治」的正當化邏輯在於,帝國與當地政治體(可能是當地的國家也可能是聚落部族)的衝突,往往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正式「戰爭」,而是不足以被定義為戰爭的小規模、零星軍事衝突。在本書裡,班頓挪用了政治與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茲的「小規模戰爭」一詞,來描繪這樣的衝突。
在克勞塞維茲與常見的軍事分析的定義中,「小規模戰爭」意指的是常規軍隊與非常規軍隊(例如游擊隊)之間的衝突。但對班頓來說,「小規模戰爭」所指的,是訴諸法秩序正當化軍事行動,依循國際法的戰爭規範(例如不會針對平民動武),卻也同時有意識地避免將軍事行動上升至國與國正式宣戰的政治與軍事衝突。這種定義的「小規模戰爭」因此不會是如同克勞塞維茲定義之下,遊走於國際法秩序與國際政治夾縫間的零星衝突,而是國際政治訴諸國際法秩序以正當化並防止衝突上升成為國與國之間宣戰的、藉由法秩序將之規範為零星衝突的政治與軍事衝突。「小規模戰爭」作為「法理政治」的延伸,在正當化政權的軍事行動的同時,解釋了為什麼和平(沒有戰爭)的國際政治秩序中,還是有政治與軍事衝突存在的現象。而本書的重要論點就在於指出,這樣的「小規模戰爭」正是自歐洲殖民以迄今日,反覆形塑國際政治秩序(而非國際法秩序)的現象。
藉由提出這樣的論點,本書不僅為國際法、全球史與帝國史研究開闢了新的重要研究途徑,也喚回了西方政治哲學與憲政理論的一個塵封已久、為人遺忘的重要論述,即商業與和平的悖論。這個悖論指出,在以商業貿易為主要政治、社會與經濟動能的世界(也就是我們的現代世界)裡,和平應該是更容易落實的,因為任何人都知道戰爭的經濟成本太高,也不利於商貿發展。然而,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裡,永久和平的理念將會變得更加遙不可及。這是因為商業社會的政治邏輯,與商業社會的經濟邏輯並不相容。經濟邏輯導向了避免戰爭,因此永久和平在望的結果,但政治邏輯卻指出,國家必須要隨時常備軍武以威嚇他國免於採取軍事行動侵占自身商貿利益。這導致的一個結果是,現代國家會常備軍隊以避免戰爭爆發、現代國家會極力避免戰爭爆發、但現代國家也因此會訴諸「法理政治」與「小規模戰爭」來強調他們所涉入的軍事衝突,並不是席捲全國的「戰爭」。
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亞當. 斯密與倡議美國必須建制聯邦中央銀行的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皆抱持著這樣的理論關懷,儘管他們可能沒有使用如「法理政治」與「小規模戰爭」這樣的詞彙。對史密斯與漢彌爾頓來說,這種悖論彰顯了一個殘酷也悲傷的現實。國際政治秩序似乎無可避免地,將會永遠存在著戰爭。差別在於,現代國家會更致力於訴諸國際法秩序來為戰爭緩頰,以避免全面戰爭的爆發。這與班頓在本書的分析一致,但本書提出了更讓人必須警戒的觀察。「小規模戰爭」的時常存在,一方面意味著現代國家有著避免「戰爭」爆發的共識,但另一方面,卻也意味著現代國際政治秩序始終遊走在「戰爭」爆發的邊緣。
在一篇訪談中,班頓明確指出了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的初期,普丁如何試圖訴諸「法理政治」的邏輯來正當化其派軍入侵烏克蘭的行動。這很可能意味著普丁試圖將衝突限縮在「小規模戰爭」的範圍,避免陷入與烏克蘭全面的戰爭。「小規模戰爭」往往是帝國限縮戰爭範圍的方法,其背後連帶的,是帝國與弱勢國家對於全面「戰爭」的恐懼與不願意「戰爭」爆發的意願。然而,當牽涉衝突的一方拒絕加入另一方「法理政治」的邏輯與「小規模戰爭」的定位時,「小規模戰爭」隨時有可能擴大成全面的「戰爭」。從「小規模戰爭」到「戰爭」只有一線之隔,而他們在本質上,真的有那麼大的差異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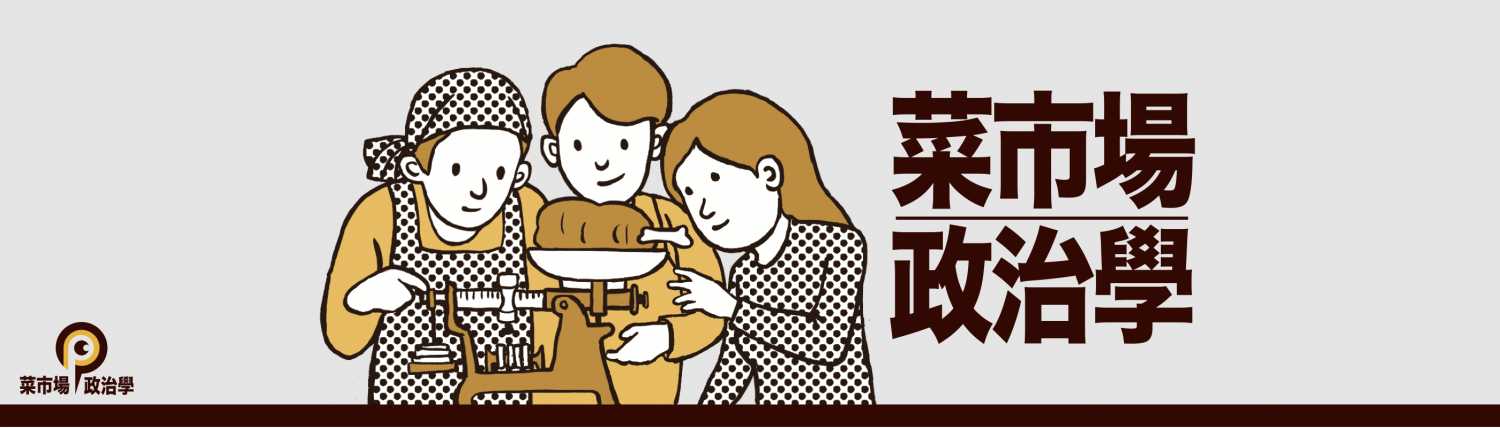
名為和平的戰爭_立體書封_有書腰_300dpi-240x30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