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彥瑜/維吉尼亞大學社會系博士生
《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六○年代的思想之路》
作者:安藤丈將
譯者:林彥瑜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8-03-14
※本文首先刊登於黑潮之聲
不知道有多少讀者跟我一樣,參與社會運動以後覺得自己並沒有改變多少社會,反而是社會運動改變了自己。

在本書即將付梓的二〇一八年,我想以一個學生而非譯者的身分,談談自己怎麼遇見這本書。我從二〇一二年開始參與台灣社會運動,徹底改變了我的價值觀。在為「睜開眼」後看見的新事物感到熱血沸騰的同時,既有的穩定生活也在或快或慢地崩解。混亂之中,二〇一三年春天,我剛好獲得系上的交換機會,到早稻田大學讀政治學。在那整整一年半的留學期間,對我而言,學的是日本,講的是日文,但是心裡想的,都是台灣。幸運的是,在早稻田大學有一群認真看待台灣研究的日本進步派學者,給我冷靜重新思考「何謂台灣」的空間與機會。
二〇一四年春天,爆發了太陽花運動。這場運動也改變了早稻田大學的台灣研究方向與台灣學生的角色:我參與一年多的若林正丈老師台灣研究專題班,從原本的歷史取向,轉為社會取向,當時,若林老師所抽換的書單之一,就是這本安藤老師的《新左運動與日本的六〇年代》。每年七月早大政經學部(梅森直之老師與若林正丈老師的專題班)與台大歷史系的交流活動,主題也改為「日本的社會運動」,其中一位講者就是本書作者安藤丈將老師,他也是梅森專題班的畢業生之一。在太陽花之後,台灣學生的角色突然變成「樣本」,回答我們對台灣社會運動的看法,分享自己參與的經驗。
也許是這些謙虛自省的日本教授與社會運動者,真的太疼惜我們台灣學生了,所以在這些「被請教」的交流過程中,我必須承認,自己的心中不由自主地養成了一股相對日本學生的優越感。好像熱衷參與社會運動就高人一等,好像日本學生只重視自己的就職就是自私一樣。抱著一個啟蒙者的心態,告訴「已開發國家」、「前殖民母國」日本,我們台灣(雖然曾是殖民地、雖然經濟不景氣、雖然無法加入聯合國等制度上劣人一等的事實)已經有多進步,日本應該要怎樣才更進步才對……。剛開始,我為這樣的交流感到興奮驕傲,因為台灣人實在太少機會能夠在國際場合抬頭挺胸地說「我們台灣如何如何」。
但過了一陣子,我不禁想,這樣的優越心態跟過往日本在殖民時期想要「啟蒙」台灣人有什麼差異呢?我能夠預設怎樣的社會是比較好的嗎?台灣難道沒有自己的問題嗎?
我再想,日本曾經有個百萬人民包圍國會的社會運動。但為什麼今日排斥社會運動的氛圍如此強烈呢?如果歷史難以預料,我們怎麼能夠有自信地宣稱台灣未來不會有一天跟今日的日本一樣呢?
我並不是抱著這樣沉重的反省心情去讀這本書,而是在讀完這本書以及和師長朋友的諸多討論之中,漸漸有了這樣的反省。我在這本書中看見太多當年日本學生與今日台灣學生的高度相似性。岸信介政權的強行通過安保條約,讓我想到國民黨三十秒通過服貿而引爆太陽花;日本學生把戰爭記憶的苦痛化為反戰運動的力量,讓我想到台灣社運中無法迴避的國族認同爭議;日本歸鄉運動中與當地鄉親的鴻溝,讓我想到自己在臉書上走不出的同溫層,以及無法對話的親戚長輩line群組中大量流傳的保守政治宣傳。
當我在讀這些日本人的行動力的時候,我真心驚訝於「這樣的日本」曾經存在過,跟我所處的日本社會,好像是完全不一樣的社會。今天的日本,在諸多社運場合,看到的多為年長者,我很難想像一九六〇年代大學生與農村人民齊聚一堂集會演講的盛況。我心想,啊,這就是日本曾經有過的「自由之夏」,才知道,在那些遙遠的歐美社會之外,東亞也曾經存在過這樣的一群新左運動者。
如果你也(曾)是運動者,讀來應該很有感覺,因為他們遇到的苦惱與抉擇,正是我們曾經或正在經歷的。這些日本運動者的行動力和反省力甚至比現在的許多台灣人還強。他們遇到的分裂問題,我們也無法迴避,像是球賽之中,敵人的陣法永遠比較穩固,自己這邊永遠手足無措。
我常問自己,如果在我之後的台灣的下一世代變得跟今日日本年輕世代一樣,我該怎麼跟他們對話?像是我的父母輩不知怎麼跟我對話一樣嗎?
縱使過往的歷史條件與今日已經大不相同,我們仍然可以從「閱讀日本」當中,找到作為台灣人能夠與之相連的魅力。對這群日本戰後嬰兒潮的世代而言,即使自己不曾經歷過戰爭,戰爭的苦痛仍被傳承下來,使得他們為反戰反安保站上街頭;對我們這群不曾經歷戒嚴與黨外運動的世代而言,民主的珍貴也被傳承下來,使得我們為自己相信的價值站出來。驅使我們行動的,是我們的共同記憶。然而,隨著時間過去,這些行動的歷史,也成了共同記憶的一部分,驅使我們繼續前進。
讀者已經從本書作者序與推薦序中知道,日本不是只有光明沒有黑暗,就像我們的台灣總是又可愛又讓人怨嘆。所以,在這篇譯後記中,我想說的是,這本書並不只是一部關於日本社會運動「失敗」的歷史,也是日本社會運動如何繼續「活下去」的過程。期待本書中文版的問世,不只能夠給予台灣讀者在社運蓬勃發展之中看見一些危險的提醒,也能夠給予香港乃至中國、以及中文世界的公民讀者們,在黑暗之中看見一些希望的可能性。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寫於夏律第鎮
(感謝左岸出版的黃秀如總編細心校正本書中譯本、以及作者安藤老師的信任與鼓勵。感謝梅森老師與叡人老師的推薦,以及若林老師在早大的指導。謝謝蘇碩斌老師的引薦與協助。最後感謝拿山瑪谷東京讀書會的夥伴一起討論本書,拿山就像是第四章的「寺小屋」一樣,伴我參與這場「學習運動」。尤其感謝許仁碩、陳威志的翻譯專業建議。)
總編輯說書:《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六○年代的思想之路》
◎黃秀如/左岸文化總編輯
反對修改勞基法、反對同婚入專法是蔡政府上台後,引發最多輿論討論、也吸納最多年輕人參與的社會運動。在此同時,推動年金改革、成立不當黨產委員會、通過公投法與促轉條例,也是在立法院激辯、街頭上抗爭的社會議題。這些因為民進黨全面執政而以為所有的公平正義就可以在短時間內實踐的社會運動卻屢屢踢到鐵板。原因是什麼?是民進黨墮落了嗎?是威權體制根本沒有瓦解嗎?是運動團體的策略錯誤嗎?是台灣社會的公民意識尚未覺醒嗎?還是那個鮮少在運動中被提起的中國因素和美國因素從中作梗呢?
如果我們想要在二十世紀的歷史找到可以參考研究並作為借鏡的對象,遠的三○年代就不用說了,和我們的文化有一段差距的西歐也不用說了,最適合拿來對照的就是我們的鄰居:六○年代狂飆的日本。同樣是受到美國支配的國家(台灣還要加上被中國影響),同樣在國內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日本是針對美軍駐日、安保條約、修改憲法、被迫進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台灣則是針對中國的經統、文統以及口頭上的武統),同樣在社會上有一群意圖透過社會運動來改變現狀的知識分子與學生(日本甚至還出現了武裝游擊隊,當然那跟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風潮席捲全球有關),同樣在從事社會運動的過程中與既存的政治社會建制產生嚴重衝突(例如大學生佔領學校、勞動者罷工、群眾包圍國會)。到了後來日本的社會運動因為過激化、暴力化、污名化而引發人民反彈,再加上經濟高度成長所帶來的消費文化把人心給馴化了,那場試圖改變世界的運動就這樣失敗了。
但真的什麼都沒留下來嗎?本書作者安藤丈將認為,當然不是。如果當年的新左運動只是煙消雲散,那麼三一一福島核災後的反核、環保、食安、反全球化、反(美軍)基地、反修憲(第九條)等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動能從哪裡來?作者試圖透過爬梳日本六○年代的新左運動歷史,證明當代活力十足的日本公民社會,正是這場運動所留下來的遺產。
※點此至讀冊網站專題蒐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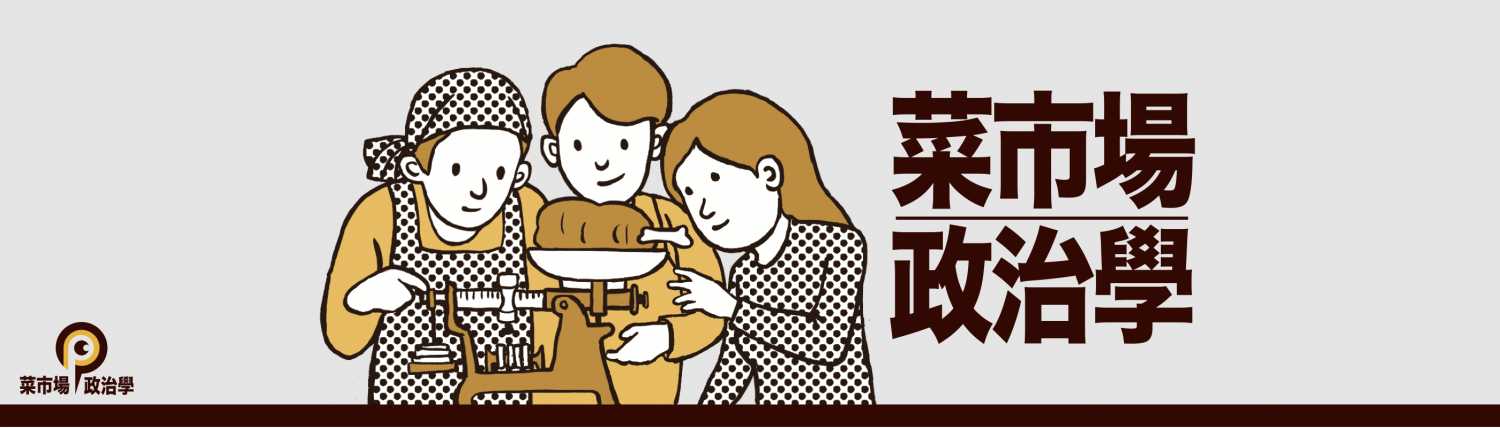
我想社会运动在其发生之时,是对既有秩序的冲击与挑战;社会运动能否成功,在于社运人士和当权者能否找到一定的共识方案,让被动摇的既有秩序在一个新的局域稳态上得以重建。中国大陆89年的事情就收场于无法达成新的局域稳态,从而导致撕裂性的结局。以及可能还要精算一下改革的社会成本:社会运动本身会消耗一定的社会成本(包括社会及政权注意力转移产生的机会成本,竞争性主张相互对抗产生的社会成本等等),而非社运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也会遇到来自官僚系统及社会的阻尼从而产生改革成本,而其各自产生的社会收益也许也可以做评估,这样可以综合计算出是否通过“社会运动”来实现社会进步,何者的性价比更高、何者更值得期待。这样也许可以解释不同世代、不同社会对社会运动态度的区别。
讓社會運動「活下去」 ──《日本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譯後記
https://yenyutw.wordpress.com/2018/01/27/%E8%AE%93%E7%A4%BE%E6%9C%83%E9%81%8B%E5%8B%95%E3%80%8C%E6%B4%BB%E4%B8%8B%E5%8E%BB%E3%80%8D-%E2%94%80%E2%94%80%E8%AE%80%E3%80%8A%E6%97%A5%E6%9C%AC%E6%96%B0%E5%B7%A6%E9%81%8B%E5%8B%95%E8%88%87%E5%85%AC/comment-page-1/#comment-11
《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作者:致台灣讀者
https://whogovernstw.org/2018/03/24/takemasaand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