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叡人/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六○年代的思想之路》
作者:安藤丈將
譯者:林彥瑜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8-03-14
“Selfish father of men!
Cruel, jealous, selfish fear!
Can delight,
Chained in night,
The virgins of youth and morning bear?
Does spring hide its joy,
When buds and blossoms grow?
Does the sower
Sow by night,
Or the plowman in darkness plough?”
—Songs of Experience, William Blake
一九六○年代席捲全球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新左翼運動,確實是世界史上極其複雜的現象。這個運動同時展現的光明與黑暗不只激烈地相互對峙,甚至還彼此交錯交融,因而產生了難解的多義性,於是無數親歷者被迫終生質問自身的記憶與信念,眾多的後來者則必須艱辛地理清那些交錯的線索,試圖讓歷史的複雜全貌展現,並且依其自身政治信念,為這個運動做出適當的詮釋與評價。
在日本這個浸透著「無常」生命觀與死亡美學的國度,六○年代新左翼運動中的明與暗,希望與破滅,愛與暴力,純真與殘酷的對峙、矛盾與交融,更是被展演到了極致,超越了同時代所有其他國家的運動。這個運動既催生了象徵希望與青年理想主義的六○年反安保鬥爭、反戰運動、日大與東大全共鬥與三里塚抗爭,但也在後期創造了他們徹底的對立面──殘酷的、絕望的暴力:黨派內鬥(内ゲバ)、私刑、爆破與海外恐怖主義。
從六○年反安保鬥爭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一月東大全共鬥的安田講堂攻防戰為止,儘管抗爭手段日趨激烈,日本的學生運動大體上依然保有理想主義的形象,一般民眾對學運也還抱持同情的態度。然而六○年代後期,學運各黨派內鬥私刑逐漸蔚為風潮,武裝革命路線也隨之抬頭後,民眾對學運觀感開始逐漸改變。一九七二年淺間山莊事件爆發,連合赤軍在山地武裝基地對同志進行私刑「總括」(清算),殺死了十數人的恐怖事件為日本社會所知後,整個新左翼學運的公共形象為之逆轉。大約與此同時,法政大學學生為主體的東亞細亞武裝反日陣線策動了一系列企業爆破事件。先後潛逃海外的日本赤軍派則與中東激進組織結合,在整個七○年代多次在各地劫機,震驚世界,成為全球新左翼運動轉化為恐怖主義的先驅,還擴散到德、義等國。經過一連串暴力事件的衝擊,學運分子在日本民眾心中的形象從熱血青年一變為恐怖的暴力犯罪者,以及公安警察口中的「過激派」。
日本學運在七○年代前期的激進化與暴力化,日後成為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遮掩了這個運動許多正面的部分,如它的理想主義、批判精神、政治與社會分析,以及文化創造。一方面,它使「新左翼」與黨派、意識形態與暴力緊密連結,成為一個具有負面意涵的語詞。另一方面,運動暴力也造成日本社會心理極深的集體創傷(trauma),使八○年代興起的日本新市民運動極力迴避任何比較強烈衝擊體制的行動,以免引發社會反感。換言之,不論在思想或行動上,運動暴力化的後果之一是妨礙了六○年代日本新左翼運動的正面遺產(positive legacy)向下傳承,使它成為一個中斷的激進傳統。二○一五年因反安保法制而興起的日本學運組織SEALDs(自由と民主主義のための学生緊急行動),就是一個缺乏與上一個世代學運傳統連結,而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出現的新生事物。新世代學運在思想與行動上溫和而自制,處處與新左翼世代劃清界線,這個特徵說明了當年的暴力陰影依然強有力地制約著日本的市民社會。
日本學生運動傳統的斷裂,以及兩個學運世代之間的齟齬,恰好與台灣成為對比:野草莓與太陽花學生運動(以及更近期的反課綱運動),是在八、九○年代學運,以及七○年代民主運動(論者所謂「遲發性學運」)的積累之上出現的,而且當代學運份子和這兩個先行世代運動者也有密切的聯繫與合作。正因為有長期運動的意識、思想與行動經驗的傳承,才會產生如此巨大的能量。弔詭的是,三、四十年來台灣學運傳統得以傳承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先行世代的學運從未像日本新左翼運動那麼激進,所以沒有造成社會負面觀感之故。筆者當年在台大從事學運時熱烈崇拜東大全共鬥議長山本義隆,滿腦子「自我否定」和「台大廢墟」論(受山本「東大解體論」影響),如今SEALDs諸君竟然受到太陽花「諸神」啟發。如同馬克思所說,人創造歷史,但不是自由創造,而是在過去積累的條件下創造的。台灣戰後初期的激進傳統在五○年代白色恐怖後斷絕,反而創造了七○年代以後溫和學運持續積累的條件,於是有今日黑潮之爆發。禍福相倚,歷史的進展,從來就不是依照直線進行的。
讓我們回到日本的學生運動。我們必須在前述的脈絡之中理解安藤丈將君這本《ニューレフト運動と市民社会》的意義:毫無疑問,這是他為了克服日本進步社運傳統的斷裂,重新連結六○年代與當代而做的一次知識上的努力。作為一位活躍在二○○○年代初期的「孤獨的」學生運動分子,他在同世代學生的政治冷漠中深深體會日本進步傳統斷裂,歷史傳承失落所帶來的負面後果。然而作為在早稻田政經學部梅森直之門下主修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博士生,他對思想與歷史詮釋對現實的形塑力量有著奇妙的信心。這本書,就是他終於選擇暫別早稻田,遠赴澳洲求學數年間沉潛思索的戰後政治史結晶。
安藤在本書中對日本六○年代新左翼運動的詮釋,幾乎完全著眼在重建進步運動歷史傳承這個實踐性目的之上。首先,他刻意選擇用「ニューレフト」(new left一詞的片假名外來語表現)而不用「新左翼」這個傳統語詞,目的就在切割與迴避後者數十年來在日本公共論述中附載的負面意涵,如黨派、宗派主義、意識形態教條,以及暴力革命等。這是許多當代日本進步左翼知識人常用的語言策略,並非安藤所原創,但是安藤並未止於語言上的再命名,他進一步提出了一整個論證,試圖將「新左翼」在大眾想像中的政治性與意識形態性格以清除或降低。他主張整個六○年代ニューレフト(new left)運動是一種戰後嬰兒潮青年世代試圖進行「自我變革」,並將自我變革連結到改變社會的倫理性運動。這種自我變革,要求改造社會要從改造自己做起,因此要從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實踐起。安藤認為,像日本大學、東京大學的全共鬥鬥爭,以及反對成田機場興建的三里塚抗爭等直接行動,本質上都是這種青年試圖自我變革的象徵。其次,他主張引發學生自我變革反抗的,是日本高度成長期日本國家與資本主義對日本人的消費性與政治馴服的規訓(discipline)。這個思考雖然呼應了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但卻有日本本土的思想根源──亦即戰前左翼思想家戶坂潤所提出的「日常性」概念。
有趣的是,安藤將六○年代後期興起的學運黨派內鬥(内ゲバ),解釋為日本ニューレフト(new left)的自我變革思想的某種過剩或延伸的結果,而非教條或宗派主義的產物。而這種過剩的自我變革要求最終導致過剩的暴力與社會的反彈,由此再誘發了警察的擴大與有效的鎮壓,最終造成了運動的退潮。此外,無止境的自我變革要求,造成了推展運動的種種實際困難,也是運動退潮原因之一。換言之,作為ニューレフト運動本質的自我變革思想內部,蘊含了促成運動衰退的種子。
很明顯,這是對日本新左翼運動一個相當非正統的詮釋,因為安藤大大地降低了思想、意識形態、宗派主義與運動組織等因素的重要性,不處理國內政治與地緣政治,甚至沒有觸及同時期全球新左翼運動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脈絡,更未論及新自由主義興起前夜的全球資本主義轉型對新左翼運動的影響。整體而言,這是一個刻意降低新左翼運動的意識形態性、政治性甚至社會性,而將重點置於個別行動者的微觀層次,而且局部的分析與重建。這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刻意選擇的策略,目的在挽救一個被遺忘的良善初衷:正因七○年代以來日本公共論述對新左翼的污名化集中在它的意識形態與政治面向,所以必須刻意壓抑,甚至清除(cleanse)這個面向,才能夠驅散陰影,讓六○年代日本新左翼運動的倫理意義──青年世代企求自我變革的理想主義,重新顯露出來。而只有上一個世代的青年理想主義被重新彰顯,才能重建斷裂已久的進步傳統,使喪失歷史意識而進退失據的當代市民運動,因重新連結到歷史母體而獲得新的生命力。
這個試圖救贖一個純真年代的詮釋有沒有成功?最終會不會達成作者企圖的實踐性目的?這些都有待時間來驗證,因為一次語言的行動,畢竟難以撼動長期歷史結構所累積形成的隔離、扭曲與惡意,尤其是像日本當代政治話語中這種四分五裂、積重難返的黨派對立。然而我們真心期待,安藤君對重建日本進步傳統強烈的執念與熱情,能夠透過這個原創的再詮釋,傳達給若干善意而認真、而且願意嘗試在閱讀這個日常行動中「自我變革」的讀者。
這個期待不僅適用於日本讀者,也適用於台灣讀者,因為我們才剛剛走過了最後的純真年代,現在我們需要沉澱、參照、理解,然後獲取經驗與知識,深度的經驗與知識。只有深度的經驗與知識才是我們的救贖,在亂世之中,我們的純真的救贖。
(二○一八年一月十九日,東大安田講堂落城四十九週年之日,完稿於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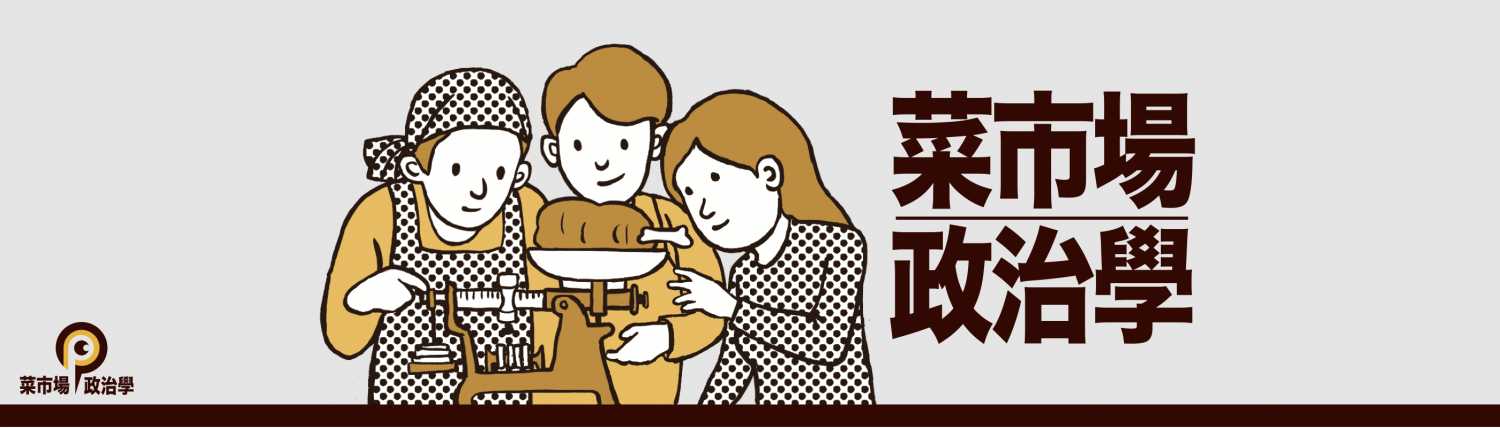

夜與霧之後 深化「日常性」的運動之路——讀《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
https://m.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80413/s00012/1523555445044
現今的日本有政治冷淡的現象,而在社運歷史年輕的臺灣,我們處在一個複雜的定位之下,臺灣的社運絕對是相比起來更為複雜,而大環境相似的日本及臺灣,日本或許能夠作為臺灣的一個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