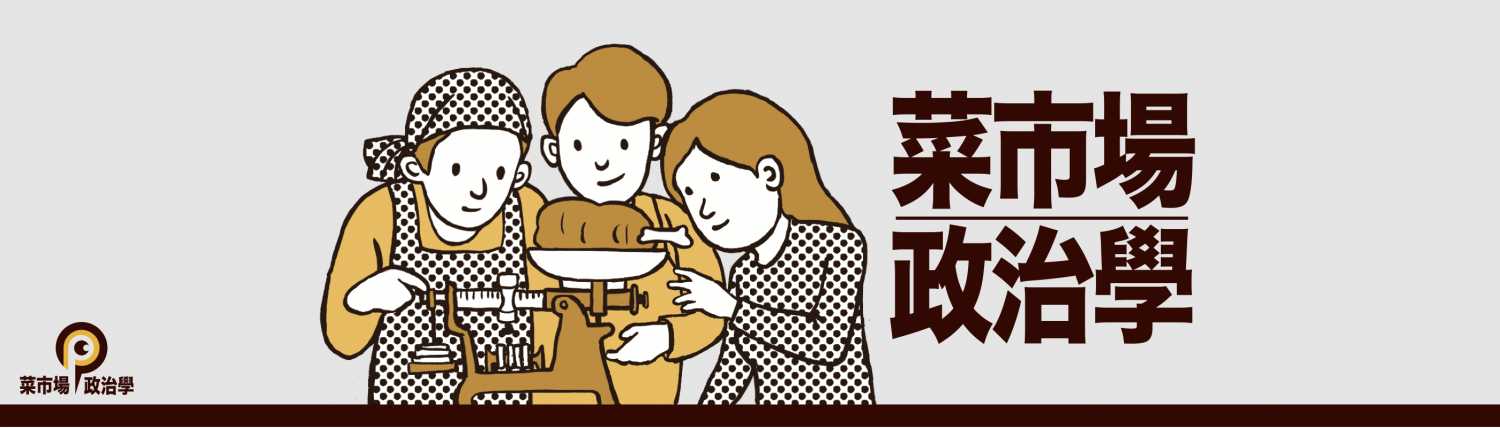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心理系與公共事務學系榮譽教授、行為經濟學領域開山始祖、《快思慢想》作者Daniel Kahneman於近日過世。Kahneman的研究對於經濟學、心理學、政治科學都有重大影響,與長期的共同作者Amos Tversky兩人一起扭轉了好幾個學術領域。
對於政治學來說,Kahneman與Tversky在1970透過一系列的行為經濟學實驗,顯示出人們在計算成本效益時並不是一直線的數學思考,進而提出由幾條曲線搭起來還會隨時改變參考點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這不僅震撼了當紅的賽局理論的諸多數學模型假設,也解釋了很多看似矛盾的政治決定。他們當時設計了非常著名的「亞洲病實驗」(Asian Disease Experiment) :假設有兩種公共衛生政策,A政策有三分之一的機率可以救全部的人、但三分之二的機率會全部病逝,B政策百分之百保證可以但也只能救三分之一的人,大家偏好哪種?多數人偏好較為保守的B,至少能保證救三分之一。
接著,又有兩種公共衛生政策,C政策有三分之二的機率會全部人都死,但三分之一的機率也可能全活,而D政策百分之百保證有三分之二會死,大家偏好哪種?結果多數人偏好去選擇有風險的C。這四種政策在數學的「期望值」是一模一樣的,但是文字敘述是正面增長時(有多少人會活)人們比較偏好保守、確定能得到的選項;而當文字敘述是負面損失時(有多少人會過世),人們比較偏好有風險、搞不好能避免損失的選項。即使在數學上理論上應該全都是等價的,但人們選擇的傾向會輕易地受到敘述方式影響。
這個結果不只說明了人天生就不是線性的數學思考,更解釋了無數的政治學現象。舉例來說,亞洲病實驗與展望理論可以推論出人們想要避免損失(loss aversion),以及對於「維持現狀」的額外偏愛(status quo):即使是違反人權的凌虐囚犯,只要在新聞上多寫一句「這政策已執行多年」,就會讓反對的比例顯著下降。同時這也解釋了包括墨西哥在內許多國家的民眾,明明知道長期執政的威權政黨不夠好,但覺得至少跟這政黨很熟了,假如換新的政黨不知道會怎樣,所以還是繼續讓威權政黨長期執政好了。這也解釋了為何執政黨往往會在競選中強調政績、強調人民正有所獲得來鼓勵大家繼續投票維持現狀,而在野黨則會強調人民正在受苦、處於損失的情境中,因此要選擇新的選項來脫離困境。
另一方面,在《快思慢想》中,Kahneman與Tversky整理了大腦的兩種運算模式,也在政治學與心理學逐漸發展成動機型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進而解釋當代的政治兩極化以及同溫層現象。簡單來說,大腦不是錄影機或維基百科、不管什麼資訊都公平的全部收進大腦裡記下來。大腦是消耗能量的,因此人們的大腦有動機去保存能量,而保存能量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使用既有常用的記憶(heuristics)跟偏見,假如覺得腦內既存的知識跟記憶已經夠處理新收到的資訊,那大腦就維持不變而節省能量(模式一)。除非真的遇到了大量破除自己迷信的新資訊,人們才終於心不甘情不願地花更多能量改變腦內的信仰(模式二)。這一系列的研究結果解釋了為何在資訊爆炸的當下,不同黨派支持者對世界的理解彷彿平行時空,也挑戰了眾多過去古典民主理論對於審議式民主的美好假設。
Kahneman的實驗設計本身都不複雜,但都能準確地抓到人們心理計算的細微之處,進而產生撼動學術領域的長遠結果,研究結果也在各地複製成功,沒有修過任何一堂經濟學的課卻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但Kahneman教授也非常和善,時常歡迎學術挑戰者來挑戰他的研究發現,其快思慢想更是長期霸占學術科普的排行榜,可以說是達到社會科學領域最崇高的學術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