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浩/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我們的語言可以被視為一座古老的城市:迷宮般的小街道與廣場,老房與新屋都有,以及不同時期加蓋的建物,外圍環繞的是無數的筆直街道和整齊樓房所組成的小區。
──維根斯坦,《哲學研究》
我看到無數相似而平等的人在原地不停打轉,追逐微小而庸俗的快樂來填補心靈。每個人都沉默寡言,離群索居,毫不關心他人的命運:對他們來說,子女和親友就是全人類!他們與同胞居住一地,卻對身邊的人們視若無睹。
──托克維爾,《民主在美國》
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
Against Democracy
作者: 傑森‧布倫南 Jason Brennan
譯者: 劉維仁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18/08/07

前言
二十世紀的天才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認為,一種語言如同一座古城,本身蘊含著一套價值觀、一種生活方式,或說一個文化,相當大程度決定了一個人或社會的眼界、認知以及情感結構,而且其中的元素有新有舊,有的甚至會在某些時代徹底走入歷史灰燼,然後在另一個時機再次以不同的姿態出現。
當然,某些字詞可能遠從他方,歷經長久的旅行才來到這一座城市,且初來乍到時,或許蔚為流行,也或許是少數人口耳相傳的稀世之珍,甚至是當權者眼中非法走私的違禁品。
政治語言亦是如此。某些過去被棄如敝屣的概念,之後卻重獲人們的重視,「民主」即是一例。作為一種政治體制,它包含了諸如「自由」、「平等」、「個人尊嚴」等核心價值,「票票等值」和「三權分立」等政治原則,以及關於「選民總是具有理性」和「絕對的權力使人腐化」等關於人性光明或幽暗面的假設。民主在過去兩千五百年的人類歷史當中,普遍且多半的時間是被否定的,但進入現代之後則成了一種普遍追求的政治理想。甚至,在二戰過後,成了國際社會公認的「普世價值」,或更嚴格地說,至少是普世人權鑲嵌於內的一種政治體制。
然而,作為一種普世價值的民主,這十年來似乎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正當性危機。雖然捍衛民主的理論仍不斷有人提出,但批評民主的書卻更加輕易地攻佔暢銷書排行榜。事實上,筆者近期走入敦南誠品時,先到政治學專櫃逛了一圈,立即映入眼簾的就有《民主在退潮:民主還會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好嗎?》、《民主是最好的制度嗎?》、《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菁英的反叛》(原書的英文標題還加上「民主的背叛」)。這些都是翻譯自外文的暢銷書,如果加上其他關於歐美民粹主義的著作,宣揚中國崛起、威權優於民主的各種標題,讀者或許會覺得,人們對民主的不滿正在成為一種新的全球共識。不意外,本書即將加添此一印象。
接軌柏拉圖「哲人王」的「知識菁英制」主張
本書作者傑森.布倫南(Jason Brennan)目前任教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商學院與哲學系,學術背景來自政治哲學訓練,專長為民主理論與公共政策經濟學,因為本書的出版而被視為政治上的菁英主義者,否定市井小民參與政治的資格,經濟立場也同樣是右派,支持自由市場。
今年不到四十歲的布倫南著作頗多,其書寫風格幽默風趣,且擅長以比喻和故事解釋複雜的哲學理論,但也好戰,至今的著作多為檄文。例如,二○一一年他即出版過《投票的倫理》(The Ethics of Voting, 2011)一書,呼籲那些欠缺專業知識的人民在選舉時千萬別去投下神聖的一票,因為他們既配不上那一票的神聖性,且留守在自己的崗位上繼續工作,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反而更大。隔年,他則出版了一本闡釋上述他個人意識形態立場的專書《自由至上主義:所有人應該知道的事》(Libertarianism: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2012)。再過兩年,他又追加了一本《何不資本主義?》(Why Not Capitalism?),直接與柯恩 (G. A. Cohen, 1941-2009)互別苗頭。長年任教於牛津的柯恩,堪稱當代英美分析政治哲學的祭酒,亦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是二○○九年出版的《何不社會主義?》(Why Not Socialism?),相當簡潔扼要地捍衛了左派的政治與經濟立場。布倫南則延伸了柯恩的推論邏輯,一一反駁他所有的主張。
讀者手上的《反民主》(Against Democracy)是上述幾本書的總結,雖然出版於二○一六年,但稍早於英國脫歐公投,是時,川普也尚未當選美國總統。也正因如此,布倫南隨後聲名大噪並被支持者奉為先知,並成為媒體競相追逐的訪問對象,聲勢直逼受邀去日本職棒開球的哈佛公知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
作為總結布倫南先前想法的本書,提出了以「知識菁英制」(epistocracy)取代民主制度的主張。其核心論旨是:民主制度的良序運作,需要每一位投票者都具備關於選舉爭議的足夠的知識,但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反之,真正影響人民生活(例如:稅制、工時與基本工資、醫療保險給付比率)乃至國家前途的重大議題(像是移民、外交和能源政策),必須交付到知識菁英的手上才真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也才安全。
畢竟,民主政治不該是讓這些欠缺知識,甚至連自己的無知都意識不到的愚民來實習的情境;據此,鑲嵌於民主制度的「平等」價值與「票票等值」原則,不但違背了人的天生智力與後天知識皆存在巨大差異的根本事實,強行落實的結果只會讓原本可以替社會做出最好、最正確決定的少數人,喪失了投票的意願,淪為知識菁英與無知庶民的雙輸局面。
欲防範這樣的政治悲劇,唯有提高投票資格的門檻才行,而具體的方式就是讓所有人進行相關的測驗,過濾掉那些缺乏社會與科學知識的人,如此一來既能確保選舉結果的品質,亦可杜絕劣幣逐良幣的蔓延!
如此看似簡單的主張,其實包含了相當多的預設與判斷,值得我們駐足推敲一番。不過,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或許有必要略述外另一個反民主並倡議知識菁英制的哲學家。這位哲人當然是古希臘大哲柏拉圖。作為知識菁英制的鼻祖,他的《理想國》是批判民主的經典之作,當中的許多概念至今仍深遠地影響西方的政治思考,而最重要的莫過於「治國猶如海上行船」的比喻:唯有專業技術才能勝任,具備任何其他特質(例如:取悅大部分的人、受到眾人愛戴)都是不適切的考量,其道理不過像人病了就該找醫生那樣簡單。
事實上,柏拉圖還真的把安定的國家類比為健康的個人。就個人而言,根據他的理解,人的心靈或說靈魂乃底下三要素所組成:理智、激情,以及慾望。一個性格穩定的人,必然由三者其一所主導,也因此有真正適合他的工作。一個社會上,慾望主導的人必然最多,而適合他們的工作就是從事生產,並藉此賺錢,畢竟,他們圖的不過是享樂。激情主導的人則應該擔任保家衛國的工作,且由國家供養,但不支薪,因為榮耀才是他的唯一追求,錢財只可能讓他腐化。作為社會的少數族群,孩子共養、女人共享的共產制度適合他們。至於那些追求真理而衣帶漸寬卻始終不悔的少數中之少數,才適合擔任治國的工作。一來,唯有他們懂得真理、何謂正義,以及值得打造的理想國度;二來,如此理解的他們,不僅視錢財如糞土、榮耀如浮雲,更理解政治權力落入烏合之眾手上的危險,大則有亡國之虞而覆巢之下無完卵,小則哲人本身的性命可能不保,正如蘇格拉底被判死刑的例子告訴我們的。
是故,唯有讓握有真知灼見的哲學家掌權,成為「哲人王」(philosopher-king),視榮耀如生命的人則擔任衛國士,而其他眾人去拼命工作、生產以換取金錢,才是對所有人都好的分工合作。人人獲取他想得以及應得的事物,當然也是個理想且正義的國度。反之,無知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則是集各種弊病與不義於一身的政治體制。
實施民主的雅典城邦,讓人民按照正當法律程序將蘇格拉底判處死刑,是鐵錚錚的事實。這是民主留給柏拉圖的創傷,也是政治哲學的起點。逃離納粹政權來到美國的猶太哲人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3)甚至據此認為,政治哲學的首要大哉問乃是:懂哲學的人與不懂哲學的人,如何共存於一個社會?更抽象地說,以批判傳統、質疑已知為職志的哲學,如何存在政治社群當中?
民主制度自古已然,於今為烈。不是嗎?

圖片:C.C. by kxz Chen。攝於2014年3月30日。
重返托克維爾的病理學與約翰.彌爾的政治處方
對此,布倫南的答案是肯定的。鑑於古代與現代民主的主要條件差異在於,古希臘民主城邦的公民之所以能關心公共事務,是因為家中有奴隸幫忙處理一切,但現代社會根本缺乏此一條件,根本不可能要求選民去理解每一個議題。此外,當代社會面臨的政治爭議,往往涉及高度專業的層面,唯有學者專家才能判斷,交付缺乏知識與資訊不足的公民來投票決定,不僅危險,也不道德。
事實上,民主原本即存在的問題,在這體制逐漸成為現代世界主流,且在愈來愈高比例的人民成為選民之後,愈是劇烈。美國開國元勳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 1735-1826)和麥迪遜(James Madison, 1751-1836)都在建國之初即深刻意識到「多數暴力」(the violence of majority)或「多數專制」(the tyranny of majority)的問題,法國革命讓此問題更加困擾政治思想家,甚至促成了新一波帶著懷舊心情的保守主義,英國政治思想家伯克(Edmund Burke, 1730-1797)是其代表人物。
不過,最深入分析此一難題的,莫過於法國政治理論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他曾兩度遠赴新大陸考察民主制度的運作,並寫就了兩卷的《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1840)。據其理解,美國的民主能運作,特別受惠於底下幾個文化因素:(一)資本主義讓人民學會為了長期利益的投資,不短視近利;(二)雨後春筍般的公司行號崛起,讓多數人學會如何為了集體利益而努力,不追求個人私利;(三)蓬勃發展的鄉鎮市議會,讓人可以從地方政治的參與,學會如何為國家盡一己之力;(四)保守的教會生活,一來凝聚了人與人的關係,二來則因為不允許女性在公領域拋頭露臉(當然也就不會出現聖女貞德之類讓人神魂顛倒的傑出女性!)所以職場上的男性能心無旁騖地工作。
托克維爾的卓越貢獻在於,讓人理解到一個政治體制的良序運作,不能缺少特定文化的支撐。然而,觀察力敏銳的他也意識到了民主在美國存在一個隱憂,那就是大眾崛起所帶來的多數專制可能性。這種專制出現的時候可能比起過往的一人獨裁來得可怕。一方面,人數本身取代了理性,成為政治的決定性因素。另一方面,伴隨資本主義而來的中產階級,加劇了人們對物質享受的看重,就算不變得自私自利,也會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紐帶逐漸在現代生活當中鬆脫,而開始追求小確幸的生活,正如本文開頭的引言所說,不再關心社會國家的命運,因為「對他們來說,子女和親友就是全人類」!
如此一來,手上握有投票權將是一件危險的事。缺乏公共意識的他們,作為選民只會投給競選時討好他們的政黨。更糟糕的是,倘若競選的承諾真的兌現,他們將在長期的政策餵養過程中,淪為「永遠長不大的孩子」(perpetual childhood)—以中國的流行語來說,亦即「巨嬰」。換言之,多數專政最後可能弔詭地讓選民自己無異於威權專制國家的順民,乃至愚民。
這是托克維爾的民主病理學。之後的就是美國歷史了。布倫南診斷的民主國家,幾乎就是托克維爾擔憂的那一個美國。至於他所開出的處方,靈感其實取自於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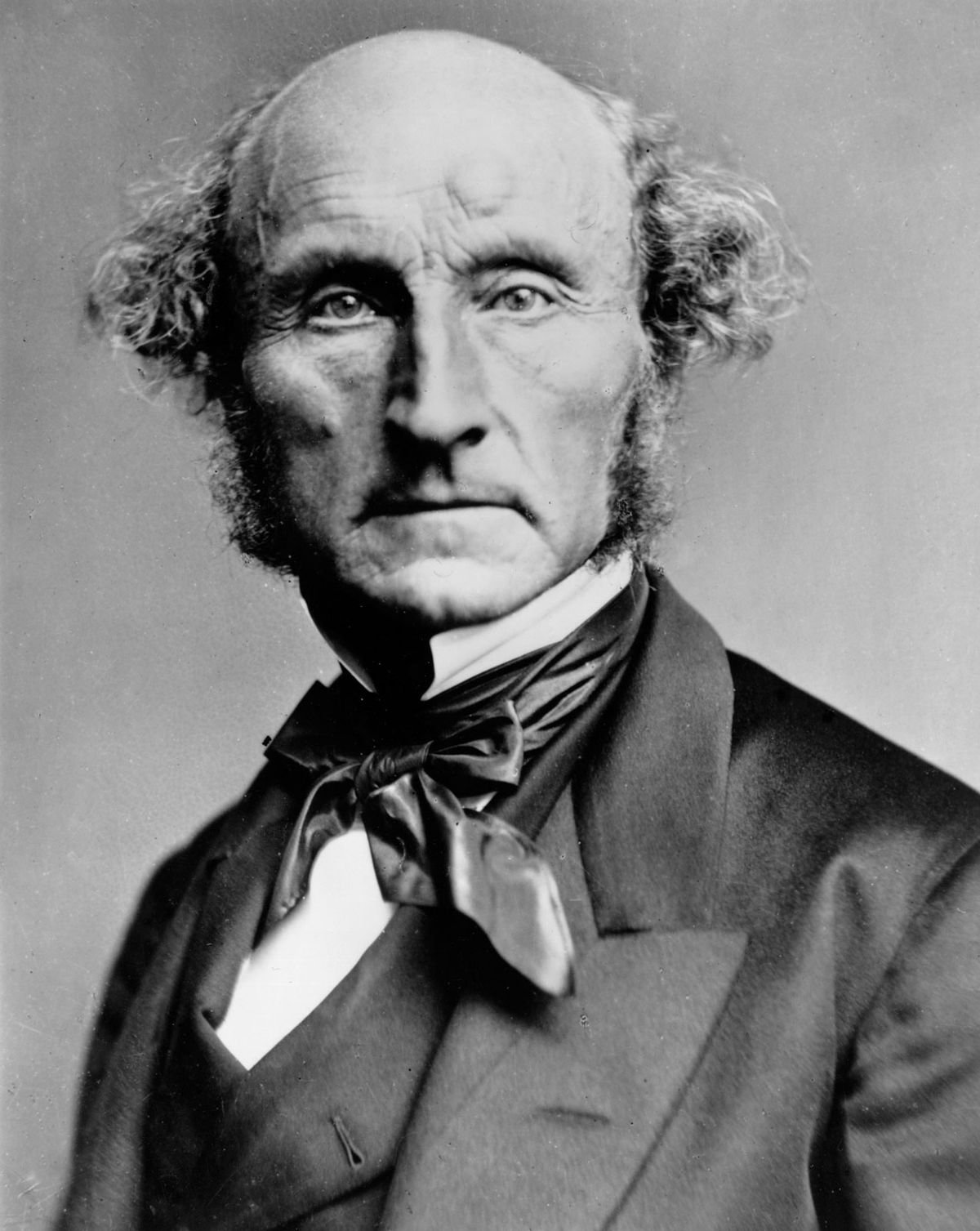
彌爾是公認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義者,終身捍衛個人自由,並提出了一套「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作為回應多數專制的問題。其主要的相關制度設計包括:首先,政府必須提供從地方到中央的完整公民參政機會,促成托克維爾所觀察到曾經支撐起美國民主運作的地方政治,也能在英國實現。再者,議會席次必須設置少數族群保障名額;此一創舉當然是對多數暴力的直接回應,為的是讓永遠的少數能有替自己發聲的機會。第三,逐步擴大選民佔人口的比例,以普選權為最終目的;事實上,他的一八六五年國會競選政見就包括了女性投票權,且成功當選。第四,以複數投票制度來作為補救選舉品質的方式;據其構想,除了每位成年人享有一張選票之外,擁有大學學歷或從事學術相關行業的公民,應當有更多的選票。
這提案並未獲得普遍支持,反倒讓彌爾被批評為菁英主義者。然而,其實當時的牛津與劍橋大學本身就是選區,因此在學的學生不但可以返鄉投票,還能在大學選區投下另一張票。這種源於大學自治傳統而產生的複數票,直到一九五○年代才被廢除。因此,彌爾的提案並非沒有事實基礎。
然而,布倫南採取了比彌爾更激進的方式,意圖將複數票的邏輯進行到底。首先,他指出民主制度本身即內建了選舉權門檻,無論是古希臘的「公民資格」(奴隸與外來移民不具備此一資格),還是現代的成年資格(例如十六歲或十八歲以上),進一步究其原因,不外是一種關於「適任」的理解;然而,他質疑:「如果你認為『十六至十七歲的人』這個族群的知識不足以投票,那麼你就必須同意低收入者、黑人也不能投票,因為這幾群人的政治知識差不多。」
相較於彌爾願意讓「不適任」的人也享有投票權,從實際參與當中來提升政治意識與判斷能力,布倫南按此邏輯則推出另一個結果:「如果不能善用權力,就請放下權力。」(見本書第八章)—按此原則的制度設計則是,不適任的人根本不該享有權力,連一張選票都不該擁有。這些人有很多能貢獻社會的方法,但投票絕非其一;同理,與其想方設法讓無能的政府下台,我們應更積極地讓他們連上台的機會都沒有,這才是保護人民不受多數專制侵犯的一帖良藥。
無論想治標或治本,布倫南欠我們一份病理報告
然而,布倫南告誡我們,彌爾開出的根本是一帖不具療效的偏方,因為選民必然絕大多數是無可救藥地愚蠢、資訊不足、在政治上過冷或過熱,持續服用政治參與,整個國家將更加病入膏肓。真正的解藥是雞尾酒療法,除了「複數投票制」之外還要加設「選舉門檻制」,以檢測科學與政治知識的方法來篩選出少數的知識菁英,再加上「模擬神喻使」的加持,才算對症下藥。
具體一點地說,布倫南認為民主制度底下只存在三種人:(一)追求小確幸,不管公共事務的「哈比人」;(二)淪為對政治狂熱有如運動賽事,把自己個人意識形態的好惡當整個世界的成敗得失,不是天天搞政黨活動就是參加社運的「政治流氓」;(三)客觀、理性,關心公共事務,願意讓證據說話,善於傾聽與溝通的「瓦肯人」。
政治哲學家提出的民主理論,基本上都預設了瓦肯人為公民。但,根據布倫南的診斷,絕大部分的美國人若非是哈比人,就是政治流氓,要不就介於兩者之間。真正的瓦肯人是鳳毛麟角,而且他們對政治缺乏熱情,也不見得傾向折衷。之所以如此,也是人們過去誤信彌爾的結果,以為政治參與可提升公民意識、增進政治判斷能力,讓哈比人都變成瓦肯人,但事實證明政治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才是對的,民主政治只會讓哈比人成為更糟糕的政治流氓;讓瓦肯人跟著更提不起熱情來參與政治。
布倫南做了診斷,也開了處方,並要求我們立即切除普選制度的毒瘤。不過,畢竟茲事體大,是否該貿然以身試藥,也許還得再考慮一下,特別是他的知識菁英制存在底下幾個疑慮。
※ 續下篇
※ 本文為《#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推薦序,聯經出版授權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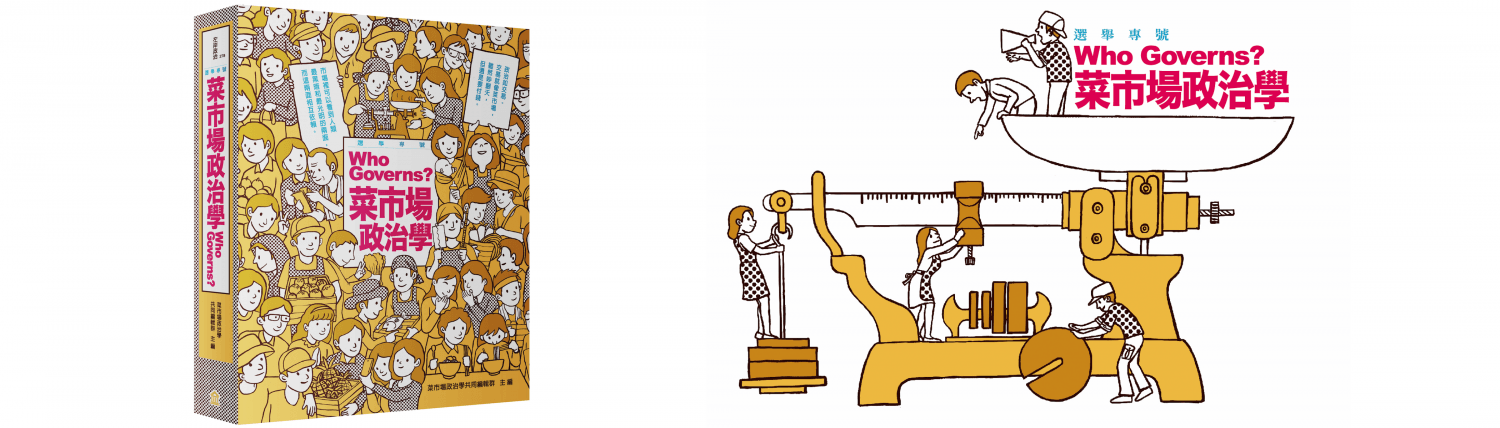
反民主論(上):選票失能、理性失調,民主制還適用嗎?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1664/3293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