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叡人/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烈火黑潮:城市戰地裡的香港人
作者:李雪莉等人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0/1
書本連結1、連結2、連結3、連結4
烈火黑潮-239x300.jpg)
《報導者》總編輯李雪莉書序:
「2019年,因為《逃犯條例》修例而爆發了扭轉歷史軸線的反送中運動。一個台灣人毫不熟悉的香港,用震耳欲聾的方式向世界、向台灣展開自我。這樣的震撼,使得許多台灣人一時半刻無法勾勒和解釋香港的現貌。怎麼理解反送中運動半年來的現象背後,怎麼認識此刻隨時處於對峙狀態下的這座城市,對台灣而言,是一份遲來卻必要的功課。
2019年6月9日反送中運動發生的當下,《報導者》採訪團隊在第一刻選擇進入香港採訪與記錄,運動的變化實在太快太強,從6月份開始認識和理解運動,到7、8月升高到進入城市戰爭的體感,之後的9月到11月則見證學生、年輕人與警方的武裝對峙。
這是一場長達半年以上(而且仍持續中)的新聞戰。高強度高頻率的跨國報導下,我們集結了一群對兩岸三地有長期關注香港的台、港、中的寫手和攝影記者共同協作 。半年間我們產出了20萬字的深度報導、數千張深刻的影像,其中不乏擲地有聲的文章和照片,透過網路向各地廣傳。當不少台灣和香港讀者開始鎖定《報導者》來理解香港這場運動時,我們決定將此系列「強權與反抗、絕望與希望」裡的文章,從更為系統和後設的角度,重新編輯成書,帶給讀者幾種理解香港的視角。
這本書之所以取名為《烈火黑潮:城市戰地裡的香港人》,是因為火焰是香港此次運動的重要意象,火魔法師在街頭在港鐵裡燃起的熊熊烈火,是憤怒是恐怖也是宣示;而黑潮則是指一身穿著黑衣戴著黑罩,如潮水般在大街在陋巷在校園甚至向山頭湧動的人龍。不論是烈火或黑潮,都與這場運動「be water」的策略一樣,柔軟又剛強,流動而堅定,隨時爆發、隨處聚合。
此刻在城市戰地裡的港人,就像滾熱的烈火、源源不絕的黑潮,抱著不願散去的意念。這不只是香港的變動,香港的故事,跨世代的香港人正牽動和影響台灣。」
菜市場政治學編按:在本書中有一篇吳叡人老師的訪談稿改寫而成的文章,向大家簡介與討論香港這個自治的共同體是如何從過去走到現在,同時放到國際的脈絡下做討論。本文很長,內容相當精彩,在這裡推薦給各位讀者們。同時,出版社提供讀者們五張限量制作的海報「在絕望中抵抗」作為贈品。
攝影:《報導者》香港特約攝影記者 陳朗熹
正面:攝於 2019年11月13日 香港中文大學
反面:攝於 2020年1月1日 香港街邊被抹掉的塗鴉
*此照片為尚未裁切的海報,貼於玻璃透光拍攝
(請見本系列文最末端的連結)

這次香港反送中運動展現出強烈的香港意識和香港人的國族認同,但傳統人文社會型的專業知識份子在這個運動裡面幾乎完全缺席。出面界定這場運動的就是運動者自身,他們並不是沒有受教育的人,相反地他們受教育的程度非常好,只是並非學院派的知識份子。我們看到他們大量地設計文宣、進行國際宣傳與遊說,裡頭充滿創意以及大量的知識內涵,這就是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講的「有機知識份子」。有機知識份子指的不是一般我們所理解的專業知識份子階層,而是在每個專業內部扮演了知識份子角色,詮釋行動意義的人物,比方說工人運動有工人自身的知識份子,他跟這個運動產生有機連結,自然形成理念的發展;所以在這場運動裡,他可能是工人,是學生,是專業的金融人士,類似這樣的專業工作者,但是他同時可能也扮演了過去我們預期傳統專業知識份子要做的那些角色。
知識份子的缺席
這些有機知識份子界定整個運動的方式真的非常不傳統。我們沒有看到如同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那樣寫出一篇《告香港國民書》,沒有看到傳統的大思想家寫一個重要的大文本來界定整個香港,沒有那些東西。看到的反而是大量的公民,用素樸的、非專業的方式不斷地自我界定,連國歌都出來了,而寫國歌的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
我比較好奇的是香港的專業知識份子在此運動裡的集體缺席。缺席的原因我觀察有兩個,一個是香港人文社會型知識份子的運動經驗非常少,非常地學院,他們是親西方的產物,一邊優越感很重,拼命掉洋書袋,一邊說自己是反殖民、後殖民,這種自我矛盾的意識非常明顯,讓他們陷入一個深度被殖民的意識裡而跨不出來。所以他們沒有辦法面對年輕人很生猛的東西,年輕人不一定讀過什麼《想像的共同體》或其他理論,卻用實際的生命在日常生活進行鬥爭。這些事情其實是嚇壞了這些我稱為「葉公好龍」的知識份子。「葉公好龍」這個成語說的是,以前有一個叫做葉公的貴族非常喜歡龍,蒐集了所有龍的畫,但一看到真正的龍現身卻嚇壞了。我覺得那些專業知識份子是葉公好龍,一天到晚在講激進、講革命,但真正革命爆發後,情況不是他們想像的那個樣子。我覺得他們跟不上革命。
第二個原因是,我覺得他們無法面對這次運動裡面,香港人爆發出來的港人集體意識,也就是說香港人覺得自己就是一個nation──或者不要用nation的話,可以用sovereign people,這個sovereign一般翻成「主權」,也可以翻成不受任何外來力量統治,是self-governing,就是「自我統治」。香港人覺得他們自己應該得到自我統治的權利(They think they deserve to be self-governing)。當然所謂「自我統治」有個光譜,可以從最高到「獨立」到「聯邦制」的高度自治。
這個東西你要叫它什麼都沒關係,叫nation、叫people,叫什麼都沒關係,但是事實上,這場運動展現出來的就是這個東西,也就是香港人的政治主體意識。這樣的意識裡最明顯的就是,作為一個sovereign people或者是作為一個nation是有邊界(boundary)的,它不可能是全人類。所以此次香港人起來抗爭有其限定的意義,在這個特定的歷史現場,香港這個共同體受到來自北京的壓力,北京試圖要吞噬香港。
我觀察到許多香港的專業人文社會知識份子,不願面對這種香港人民族或國族或政治主體意識爆發的事實,陷入了某種我稱為collective self-denial,也就是集體的自我否認的困境之中,以致於不知如何去面對這場革命,也不敢去承接歷史藉由這場革命向他們提出的任務,最終導致了集體缺席的狀況。
很多香港的知識份子如同徐承恩所講的,陷入一種「虛幻的都會主義」。香港那些受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常常自以為香港是西方先進國家的一員,自以為自己是法國、美國或英國的一部分,屬於廣義最進步的歐美知識圈的一環,可是他忘了香港其實不過是中華帝國底下的一個殖民地而已,事實上只擁有極為有限的自治權,而且還不斷地被侵蝕。
過往的高度自治是一種被恩賜的善意
香港過去在港英時代享有的高度自由跟法治其實是一個過渡狀態,一個無法持久的現象,它必須建立在統治者的善意之上。英國統治者願意給你,你就有;他們走了以後,中國統治者不給你,你就沒有了。但是香港的知識份子還陷入一個幻想,以為那是他們固有的東西,但那個不是固有的,那個是被恩賜的東西。
在香港虛幻都會主義的知識份子眼中,追求政治主體的意識,比方說民族主義或者自決這類想法,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右翼的、是保守的、是排他的、是壓迫性的。但西方知識份子在批評民族主義的想法時,他們已經達到了自治的階段,他們已經獲得了自治權;在獲得自我統治權之後產生了「過剩民族主義」(excessive nationalism)的現象,使得民族主義從抵抗的變成官方的民族主義時,如此就會產生壓迫。
民族主義有兩面性,作為一種弱者的抵抗形式,它的正當性是很高的,例如左膠最喜歡談的法農(Frantz Fanon),就主張民族意識動員是反殖民運動必要而不可避免的過程。但是如果變成官方推動的民族主義就容易產生壓迫。一般在講的是這種以國家力量去壓迫差異、他者,對這種現象我們會批評它是一個過剩的東西。但是香港人連前者(自治權)都還沒得到啊!老實講,他們連百分之一的自治權都還沒拿到。
民族主義並非全部都是邪惡的,它善惡兼具,你要在每一個個案裡面去判斷,到底這個民族主義的特性是什麼。
香港這次的運動很明顯是一個抵抗性、防衛性的東西。在歷史的進程上,香港人還沒拿到自治權,所以他們想去奪取自治權(雙普選或獨立),至於拿到自治權後接下來會怎麼樣,包括以後如何界定香港人,包含對移民的態度,包含香港內部各族群之間的關係,資源分配等等,可以再討論。
香港「準國家」地位的形成與錯失
那回過頭來看,香港人怎麼形成?有沒有一個共同體的成形過程?
香港人的形成有幾個階段。第一個,英國劃定了香港領土邊界。英國一開始拿到香港本島,後來拿到九龍、新界、大嶼山島四大區,現在我們講的香港邊界是十九世紀後半在英國統治下形成的。
第二個,是劃定了香港人的邊界。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因為中國革命,香港在五〇年代就設定邊界不讓難民進來,他們發香港身份證,辨識誰是香港人,那是四九年革命以後的事情,確立了誰是香港人。
第三個,是英國各種建設。特別是一九六七年的「六七暴動」以後,到了七〇、八〇年代,當時的香港總督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做了許多「我愛香港」的建設,希望強化香港人的認同。
在英國統治下,英國給香港殖民政府接近於獨立國家的權限。大英帝國對於自治領地通常給予類似準國家的身份,讓他們在國際上以一個政治實體的身份活動;所以香港可以跟其他國家簽條約,可以參加國際組織,有自己的國際通訊碼,有自己的護照,還可以在很多國家派商務代表。在很多面向看,香港幾乎可以說是一個準國家。
你可以看到的,不只是劃定領土的邊界,確立人民的邊界,然後創造認同,同時把整個香港人納入一個準國家的架構裡面。香港的市民不只是市民,香港的市民同時也具有國民的意義,香港人其實就是香港這個準國家的國民。
一九四七年,香港在二戰後的第一任總督楊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當時有一個計劃想要強化香港人的認同,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給他們參政權,不過這個計畫未實現他就離職了。五○年代中英建交後,周恩來恐嚇英國人說,若讓香港人有參政權,就要打香港。為什麼?香港人一旦有參政權,就一定會獨立了,要是港人拿到參政權,就不會想要再被北京管了。
中共成立之後,跟大英帝國有一個彼此理解,就是不要給香港太多人權利,不要推任何自治。因為香港是一個軍事上無法防守的地方,但大英帝國又不想放棄在遠東的重要據點香港,為了保留香港就得取得中共的同意。這是香港為什麼沒有辦法像其他英國自治領地一樣有自治權,最大的原因就是中英之間這個默契的結果。
之後是一九七一年中國加入聯合國以後,中國最早做的一個動作,就是在一九七二年成功促使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把香港從殖民地的名單中拿掉。中國在加入聯合國以前,香港還是在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y的名單上。當時根據聯合國的定義,如果你在這個名單上面,是有自決權的,而這些被聯合國認可的殖民地可以經由公投獨立或是託管獨立等過程,取得獨立的地位。中國進聯合國後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把香港從這個名單拿掉。
你可以看到,兩次歷史的機會被拿走了。一次就是英國戰後初期,打算透過賦予香港人參政權的方式強化對香港的認同,但被北京阻止了。第二個是從國際法上,把香港作為殖民地所擁有的自決權拿掉了。
然後第三波就是中英談判,當時民間的多數民意其實是想繼續接受英國統治的,八〇年代中英談判的時候做過幾次民調,想要留在英國統治下的人數是最多的,遠遠超過回歸中國的人,但是沒有人出來表達這個聲音。而站出來為香港人發聲的知識份子,基本上把一切都賭在中國的民主化。這是有時代背景的,因為一九八〇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那是最自由的時代,劉曉波、甘陽那些所謂自由主義者就是在八〇年代成熟的。但到了八八年、八九年的學生運動爆發,中共卻做了一個決定,就是「我要鎮壓」。這是一個歷史的分歧點,中國如果決定經改、政改並進,今天中國就不一樣了。我認為當初八〇年代,包括李柱銘在內的很多香港知識份子,在參與中英談判的時候,相當程度是賭在中共自由派領導人如趙紫陽等人身上,但是賭注失敗。
被中國「內地延長主義」搖醒的政治意識
香港人的政治化,也就是比較積極追求政治參與的想法,大概是九〇年代開始清晰的。嚴格講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大概是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開始,英文叫rude awakening,好像硬被搖醒一樣。六四天安門事件突然讓香港人意識到他們必須要想辦法思考自己的命運,必須自救。所以在英國統治的最後五年,就是從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七年,彭定康(Chris Patten)努力地想要讓香港民主化,香港人也很積極想要追求民主,但為時已晚。彭定康做了一個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參政權賦予,雖還沒有到完全地賦權,但已經有很高程度的參與,可是這個幾乎接近於普選所選出來的第一屆立法會,卻在九七年之後馬上被解散,由北京另外派一個,香港局勢整個就被逆轉了。
而一切在九七年之後歸零。九七年是一次reset,重新來過。香港原本對中國還是期待,期待中共對一國兩制,對《基本法》的承諾,尤其是雙普選的承諾,結果沒有想到中國對普選的理解跟你完全不一樣,中國的普選是控制型的選舉。結果期待不同的雙方衝突慢慢開始顯露,到二〇〇三年最劇烈,也就是第二十三條國安立法引起的五十萬人大遊行,這是香港自決運動的第一次大規模動員。雖然中間有一個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突然之間中國的官方民族主義把香港人動員起來,產生一段短暫的親中過程,可是馬上就冷卻了,然後接著本土主義就整個爆發出來。
一開始是從民生層次爆發的,從民生、土地、房地產開始,主要問題在於香港人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命運。你可以明顯看到一個共同體無法控制自己邊界的結果,就是讓外部滲透進來,最終導致一個共同體的崩潰、瓦解。
現在我們偶爾看到香港人會在自己的土地上排斥中國水貨客或中國投資客,但是我們要理解排他的脈絡,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排他?因為香港人覺得失去了對香港邊界的控制權。
第一個是移民政策,香港人無法控制,由北京控制。北京決定哪些人可以透過單程證移進來,二十二年來移進至少一百零三萬人;另外一個是觀光客,他們進到香港的這些頻率也是由北京控制。中港之間要整合到什麼地步,整合的速度要多快,也是由北京控制的,你可以看到大灣區的構想和規劃很早就開始了。換句話說,它從一開始就在預視把香港融進中國,是從全中國南方的區域發展角度、東南沿海的區域發展角度去設想香港的角色。香港本身的特殊性不重要,如何跟整個周邊融合更重要,於是才會搞出那一套類似「內地延長主義」的整合計劃。
日本統治時代對台灣的策略也是內地延長,目的在逐步把台灣整合到日本母國裡面。中國對香港的態度就是一種逐步的內地延長主義。內地延長導致各種後果,最嚴重的是人口結構的改變,「雙非嬰兒」等政策是讓香港無法控制自己的邊界。這使得香港內部的資源分配受到嚴重的干擾,北京可以用各種後門重新創造新香港人,而整個過程沒有經過香港人的同意,是單方面決定的。
香港的社福資源原本就非常少,現在更慘,雙非嬰兒是一個,住宅的問題也很嚴重。至於水貨客,他們並沒有香港的永住權或者公民權,但是他們可以進來大量收購香港的民生用品,也嚴重干擾了香港人的生活。
我們看到了包括「光復屯門」、「光復上水」這一類的行為,其實是中港強制合併跟融合過程裡面,引發的較低端的、表面的衝突。香港人能夠做的事情也就是這樣而已,他們無法要求「你最起碼要先問我要不要同意」。香港人沒有辦法自我統治、沒有主權,無法控制自己邊界的結果,是導致了自己邊界不斷被侵蝕,整個社會不斷在崩解。
這裡面的崩解面向很多,還包括中國資本進來。那些資本進到香港,除了炒房地產之外,就是在香港開發跟投資,激烈地改變香港的生活型態。香港的各種街角地貌,各種老店、小店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堆迎合觀光客的大連鎖店,改變了原來香港的味道、原來的地景,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這一切都被改變了。那最終就是文化認同也會改變。
另外是粵語的問題,就好像日本當時在台灣一樣要消滅台語。中國在香港,很明顯要消滅港式粵語,所以它搞「普教中」,你有沒有注意到現在香港年輕人的北京話好多了?這就是近年語言同化政策的成果,雖然廣東話還在。
我可以說,包含年輕人「光復上水」這一類的行動,其實是非常無奈、很低層次的抵抗。因為他們無法在源頭管控自己的邊界,他們只好直接用肉身去衝突、抵擋。
你可以看到北京跟香港一國兩制這二十年來,表面上是維持一國兩制,實質上是要把它用內地延長方式逐步把你同化、整合,把你消化到大灣區裡面。香港自身的特殊性完全不重要,對中國而言,香港最終就是要實質上融進大灣區,但形式上仍然維持一個特區,目的是當中國跟世界之間連結的白手套,接收資金,還有他們洗錢的管道。
如果你是香港人,你會怎麼想?香港可以說大概是從十年前開始,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以後開始出現本土主義。從前面這個角度來理解,你可以看到這十年來香港本土主義的本質是防禦性的,一開始是一種很純粹地保護本土,到後來逐漸升高到民族主義自決,但從頭到尾都是想要抵抗北京的同化、整合壓力,防禦香港社會和認同。
其實香港菁英對這點是知道的,但對他們而言,最大的困難是你要不要跟一國兩制這個體制決裂,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政治決裂」的論述在後雨傘時代初期整個出來,並且達到了高潮,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梁天琦二〇一六年參選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喊出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從剛剛講的那個脈絡去看,本土主義會起來,一開始是在日常生活當中衝突,例如反水貨客或雙非,結果逼出了「蝗蟲論」的說法,這些很明顯都是防衛性的,但是只要你往深層去思考為什麼這些雙非、水貨客、觀光客會出現,當然就會注意到中國要把香港最終整合進去的政策了。梁天琦的主張,很明顯地是一種「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的民族主義,但這是先前幾年本土主義抵抗北京整合壓力過程中,迅速政治化的必然後果。不過二○一八年梁天琦被判刑入獄,香港民族黨被宣告非法之後,這條激進決裂的路線暫時被壓下來了。
中港融合的政策導致前面說的那些現象出現,先在末端產生衝突,接著再往上延伸。大家慢慢發現整個問題的根源原來是在政治,所以香港人要求拿回政治的決定權,香港人覺得當我們可以雙普選,可以控制立法權跟行政權,然後司法又是獨立的,北京就不能隨便送人進來了吧,北京做什麼都要跟我們協商。這是多數香港人的如意算盤,沒有要獨立,只要雙普選、一國兩制、《基本法》就好了,所以很多香港的知識份子把《基本法》當作他們的小憲法。但北京一點都不把它當成憲法,北京把它當成一個比一般條例還要低的東西啊!它可以任意干預,而且干預愈來愈強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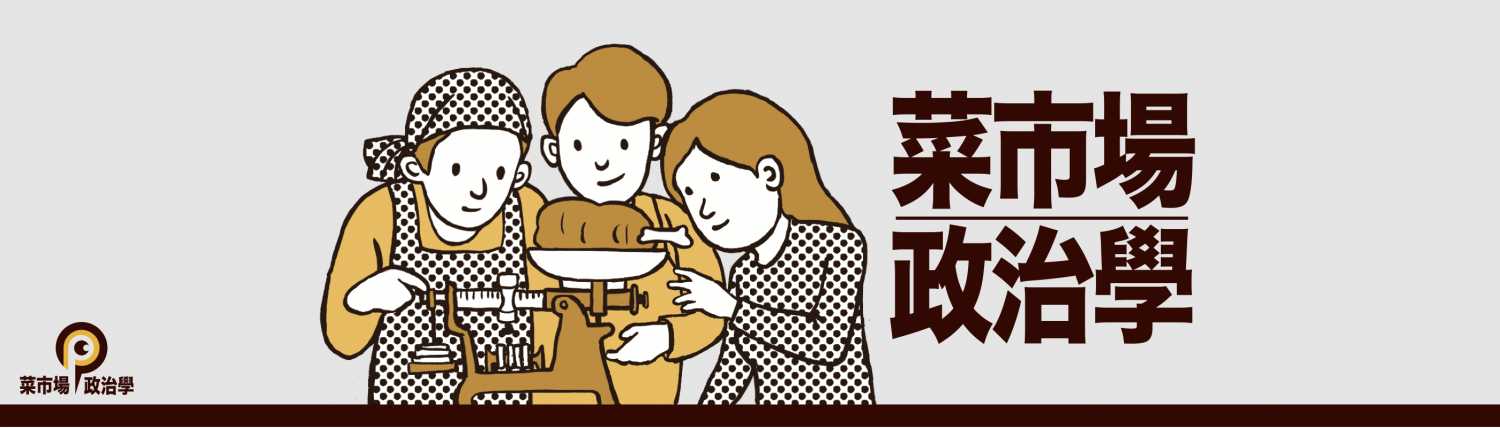
從變遷看北京治港人事與機構調整的意涵
https://tw.news.yahoo.com/-yahoo%E8%AB%96%E5%A3%87%E8%95%AD%E7%9D%A3%E5%9C%9C%E5%BE%9E%E8%AE%8A%E9%81%B7%E7%9C%8B%E5%8C%97%E4%BA%AC%E6%B2%BB%E6%B8%AF%E4%BA%BA%E4%BA%8B%E8%88%87%E6%A9%9F%E6%A7%8B%E8%AA%BF%E6%95%B4%E7%9A%84%E6%84%8F%E6%B6%B5-230009785.html
Thx for sharing.
香港加油,你們不孤單,台灣人會支持著,與你們一起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