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延續了作者桑格長期以來對美中科技戰、威權擴張以及民主防衛的觀察,討論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陣營如何因應中國與俄羅斯的挑戰。本書的中文譯名是「捍衛西方之戰」,但在英文標題當中(副標題China’s Rise, Russia’s Invasion, and America’s Struggle to Defend the West),文眼在於struggle,這個字除了奮鬥、競爭之外,還有「掙扎」的意思。作者開宗明義就指出,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一段長時間的「歷史假期」已經結束,目前全世界面臨的是中國的崛起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所帶來的挑戰,要應對這些挑戰並不容易。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劇變的當下,本書詳細討論了變化的過程,包含許多第一手的訪談資料,還有很多有趣的報導場景,從這些人物故事與互動過程來看整個世界局勢的變化。
讓Tilly重返教會?中世紀宗教與歐洲國家分裂的根源

在當代社會科學界,學者Charles Tilly的「戰爭製造國家」是頗具影響力的觀點。Tilly認為歐洲現代國家的形成,起源16至18世紀後,各國君主由於戰爭動員的需要,將封建體制逐步汰換,當時多場大型戰役促成歐洲各國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機器,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至此出現在人類眼前。不過,近期史丹佛大學政治系教授Anna Grzymala-Busse發表在政治學頂尖期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文章,提出一個新觀點修正Tilly的解釋。在今年美國政治學會年會將召開前,學會並宣布該文獲頒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當年度(2024年)最佳論文獎。Grzymala-Busse在該文主張,要理解歐洲近代國家的形成,必須找回中世紀的宗教政治(羅馬天主教會),對當時歐洲國家體系趨向分裂的長久影響,並重新評估Tilly「戰爭機器」國家理論的侷限。
《幻象帝國:天朝中國的自我神話與天下敘事》台灣版推薦序:一部總結「習近平上半場」的作品
0GGK0403幻象帝國-立體書300dpi-270x270.jpg)
法國新聞工作者董尼德的《幻象帝國》,則是一部總結了「習近平上半場」的作品。「上半場」指的是習近平自接任總書記到二○二五年中為止。在十二年前,因著胡錦濤「一次全退」的決定,習近平得以在二○一三年初名正言順將黨、政、軍三大權力一次收攏到自己身上。今時今日回顧這個關鍵時刻,確實可以發現從胡錦濤到習近平,是日後中國政治、社會文明發展的分水嶺。胡錦濤、溫家寶執政時代,中國在商業經濟上致力從世界貿易組織(WTO)之門融入世界市場;對內治理上,網際網路和媒體還有監督、議論的空間。無論公共知識分子推動的「新公民運動」,或者民間律師倡議「依法維權」,都為中國的體制改革留下了進步的可能。但從胡、溫到習,不只是人事的更替,更是執政路線的大轉變。文革結束後,一般論者同意中國經歷了兩段較為開放的時期,第一段是一九八○年代,第二段是兩千年前後。但習近平一掌權,中國的第二段開放時期迅速收縮終結。胡、溫執政時期,中國國力快速增長,但尚且以「和平崛起」來敘事。到了習近平掌權,依靠經濟收買和武力脅迫的對外擴張成了中國對外關係的主旋律。這是《幻象帝國》整部作品的基調。
小國對於大國的抗衡策略:以台灣和波羅的海三國為例
《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序論:巨浪、餘生、火種
女人賦權女人:再探婦女保障名額的影響

今(2025)年初,臺灣女性參政迎來可能的關鍵變革。婦女新知基金會等團體聯合立委召開記者會,呼籲修正《地方制度法》,將現行「四分之一婦女保障名額」調整為「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除了確保更多女性能夠進入政治場域,也讓過往僅保障女性的制度設計在未來也有可能保障到男性。幾週後,內政部長劉世芳也表態,內政部正研擬相關修法,希望讓保障名額成為促進性別平等的推手。然而性別配額究竟發揮什麼作用?它真能改變政治權力結構,帶來更具包容性的政策?還是如反對者所言,只是一種裝飾?當保障名額增加,又如何影響政治菁英組成、政策設計,甚至民眾的態度與行為?臺灣大學樊家忠教授、劉錦添教授、臺北大學陳妍蒨教授與本文兩位作者何雨忻、李易修發表於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的新文章,揭示了婦女保障名額的重要效果,這項早已寫入憲法,並且在臺灣地方選舉施行超過七十年的制度設計,不只推動更多女性走入政治場域,更改變了社會整體的性別態度。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陰暗和挑戰

2013年9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的納札爾巴夫大學發表演講,援引古代中國漢朝張騫兩次出使中亞為例,倡議用創新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計畫的濫觴。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說提到,15世紀明代航海家鄭和七次遠洋航海證明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國政府設立的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合起來稱為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遍布亞洲、非洲、歐洲、美洲和大洋洲,共計154個國家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計畫提供給合作的國家基礎建設和發展資金的目標,是可以幫助這些國家改善交通和生活的品質並促進經濟成長。然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合作的國家也出現債務高築或是以領土租借給中國以抵債的悲慘狀況。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為何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執行會出現挑戰面和陰暗面、一帶一路倡議產生最多負面衝擊的國家以及中國如何透過一帶一路的計畫來達成其地緣政治利益和可能遭受的挑戰。
《台灣六位總統剖析》書評:典型「黨國觀點」的示範

最近筆者受國際期刊編輯的邀請,為康培莊(John F. Copper)教授的新書Taiwan’s Presidents: Profiles of the Majestic Six寫書評。本書透過訪談、個人紀錄、以及資料分析,為台灣的六任總統做紀錄以及評論,從兩蔣時期一直到蔡英文(不含中間短暫接手的嚴家淦)。不管從政治學或者歷史學的觀點切入,這本書都會提供台灣研究一個很好的素材。而本書作者最特別之處在於,在作者序就開宗明義特別強調,作者本人親自見過這六位總統,因此可以提供很不錯的第一手觀察。作者指出,本書的目的是要解析六位總統獲得權力的過程、執政時面對的重大挑戰,以及分析他們執政的成績,做一個功過的評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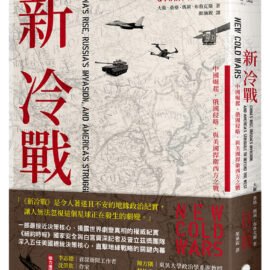

0GGK0400巨浪後-立體書-300dpi-270x270.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