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有一波關於「台灣自我防衛決心到底是高是低」的討論,這個問題在美國的政策圈也常常被問到。美國不少研究兩岸關係的人們都很好奇,到底美國的承諾會有什麼樣的效果?美國「承諾在危機時刻提供軍事協助」是否可以提振台灣士氣以及人們的參戰意願仍是一個未知數,過去還沒有人做過這樣的研究。透過民調實驗,我們發現美國的軍事協防承諾,確實能顯著地增加人們的自我防衛意願。
美國的安全承諾會影響台灣人們自我防衛的決心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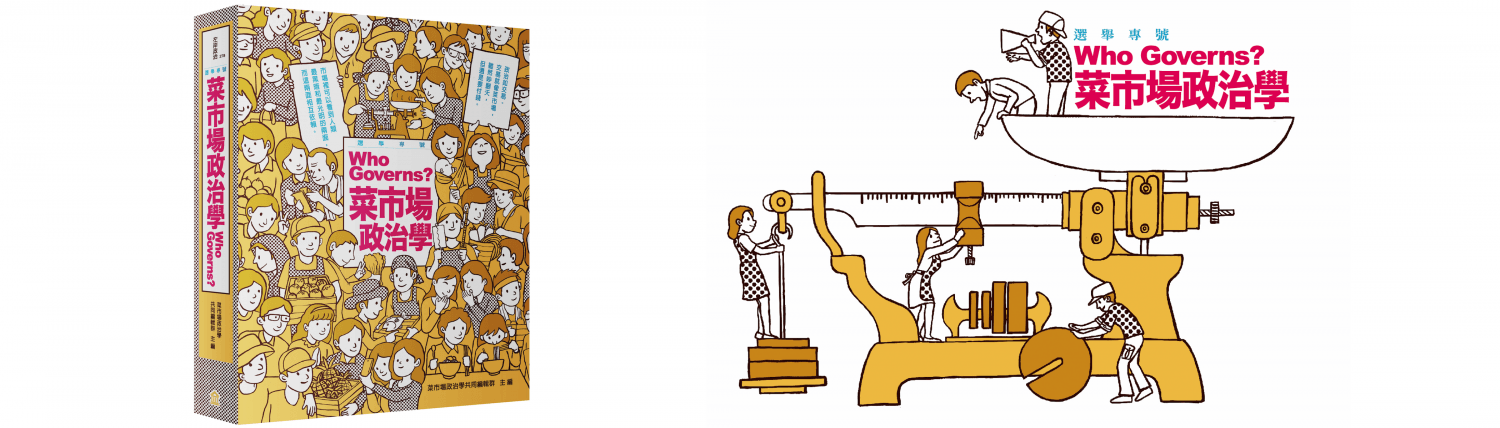

前陣子有一波關於「台灣自我防衛決心到底是高是低」的討論,這個問題在美國的政策圈也常常被問到。美國不少研究兩岸關係的人們都很好奇,到底美國的承諾會有什麼樣的效果?美國「承諾在危機時刻提供軍事協助」是否可以提振台灣士氣以及人們的參戰意願仍是一個未知數,過去還沒有人做過這樣的研究。透過民調實驗,我們發現美國的軍事協防承諾,確實能顯著地增加人們的自我防衛意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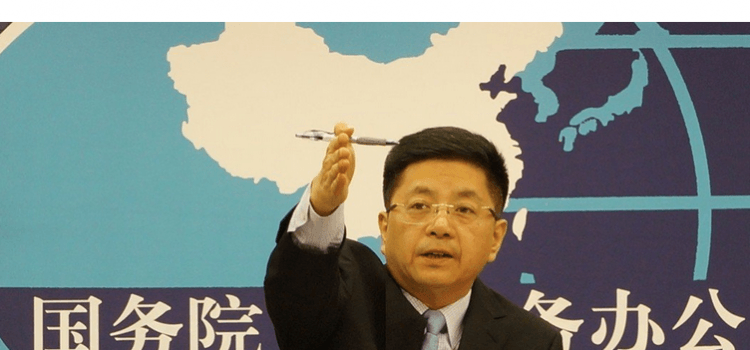
新任高雄市長韓國瑜在當選之夜發表談話,首要重點強調九二共識就是他的意識型態,要馬上成立「兩岸工作小組」,讓高雄可以「條條道路通賺錢」,隔天,新任台中市長盧秀燕、南投縣長林明溱也立刻跟進。大家有沒有覺得九二共識這個詞好熟悉?是的,從2008年兩岸開始用這個詞以來,這個詞在兩岸關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近幾年來,因為蔡英文當選總統後不承認九二共識的存在、只說1992年有一個歷史性的會談,因而受到中共祭出縮減觀光客、中止官方接觸等手段來抵制兩岸觀光的發展。因此,至今仍有非常多人呼籲台灣要趕快再(重新)承認九二共識以改善兩岸關係。不過,在做這個決定之前,我們應該先了解,九二共識的內涵是什麼?

在一場選舉當中,如果出現了一位立場比較鮮明、在光譜上面比較極端一邊的候選人,將如何影響選舉結果呢?對於主要大黨來說,該怎麼面對這樣的「側翼」對手?他們會把立場比較鮮明的選民都給吸走嗎?若從現實生活的例子來看,我們要怎麼解釋2016年大選時,民進黨選擇在立法委員選舉跟被認為是光譜上「同一邊」的時代力量合作,不怕被搶走選票嗎?

史丹佛大學政治學教授法蘭西斯福山今年出版的重磅新書《Identity: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在前言就直接說他要面對兩大問題。第一,他要回應他自己曾在蘇聯倒台後提出的歷史終結論為何仍未終結,以及這些年來批評者對他的誤解;第二,他希望可以解釋為何川普的當選與民粹主義浪潮,是在「現在這個時候」,才在全世界各地出現。本書的整個理論架構,來自三大因素的匯流:(1)人類隨著歷史逐漸變化對於尋求尊嚴的天性; (2)歐美國家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尤其在蘇聯解體之後; (3)快速的工業化與全球化。三個因素的匯流導致了民粹主義長期伏流,卻在近年來忽然崛起。

無論美國或台灣,近年來數量陡升的「無黨派選民」都是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根據美國杜克大學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每年固定執行、全國電話抽樣的國家安全調查中,2017年是史上第一次,台灣有超過半數的選民認為自己「不屬於任何黨派」。過去會有泛藍執政就綠增藍減、泛綠執政就藍增綠減的正常平衡現象,在2015年以後卻未曾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台灣民眾越來越多人同時表達不支持過去被標籤為泛綠或泛藍的政黨、甚至也不支持任何新興的小黨。

最近年底地方選戰逐漸加溫,尤其最熱鬧的台北市長選舉更占盡所有版面,各候選人的支持者與反對者無不時時刻刻緊盯著各網站平台各地征戰。但就在熱戰方酣的當下,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情景:整個八月,全國所有媒體,沒有任何關於台北市長選舉的民意調查!有趣的是,同樣是選舉前夕,四年前八月各個媒體跟團體至少公布了6次台北市長民調結果。而今年八月的另外幾大都市市長選舉也都有新民調數字。

隨著年底地方縣市議員選舉日逐漸接近、各黨的提名也逐漸確定,候選人之間激烈的競選與合縱連橫也敲鑼打鼓地展開。由於執政的民進黨在台北市選情在民調上尚未起色,而最大在野黨國民黨也被說是在打佛系選戰,兩大黨支持者甚至幹部都擔心這無法起到「母雞帶小雞」的作用。等等,什麼是母雞帶小雞?

隨著年底地方選舉越來越接近,各家民調滿天飛,各政黨也常透過電話民調來決定要派誰代表黨出馬參選。然而,各家民調公司在進行電話民調時,大多是透過電腦自動隨機撥號,看要做哪裡的民調就撥哪裡的區域號碼,後面數字隨機打七個。然後,讀者你馬上就也看到一個大問題了:「家裡沒電話只有手機的人怎麼辦?」的確,很多在外租屋、在外就學、在外工作的菜市場讀者都跟我一樣,家裡根本就沒有電話,因此一般依據市話來進行民調的公司根本聯絡不到我們。但是這樣的「純手機族」到底有多少人呢?聯絡不到純手機族,是否會顯著造成民意調查的偏差呢?

隨著赴中留學的台灣人數上升,新聞或網路上都對於這群台生的決定與未來有不少討論,也衝擊到國內政治與相關教育政策。但對於這群台灣學生,在前往中國讀書之後,到底會有怎樣的轉變?這個問題也是許多學者、乃至於兩岸官員非常感興趣的問題。

隨著中國政局變化,中國政府在2018年4月1日再度加強翻牆的難度,讓翻牆軟體vpn更難使用。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也對網路上的各種內容審查更為嚴謹,讓使用者超過兩億的今日頭條CEO出面道歉內容審查不夠。到底中國民眾本身是怎麼看待網路長城的呢?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實際上要做起科學研究非常困難,因為第一是中國政府不會讓你問這個問題,而就算問了,受訪者也不一定會講實話。